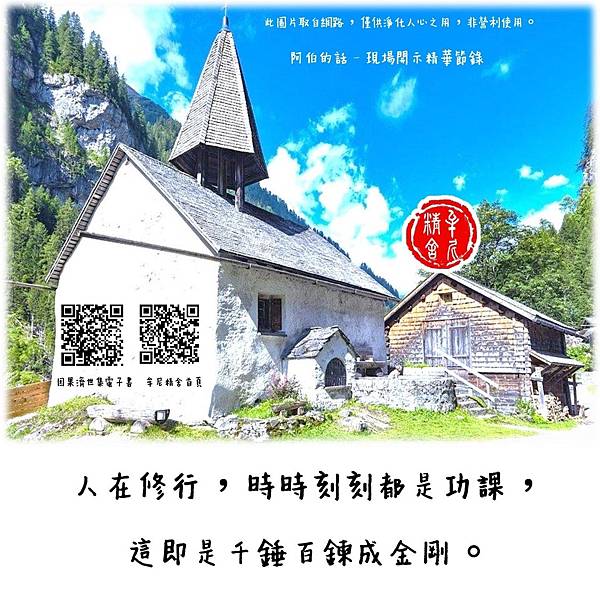上一章提到「成為受方」與增加「受」的機會,在數學上有一個很著名的提問,稱為三門問題,或是「蒙提霍爾問題」(英文:Monty Hall problem)。

在這裡談這個話題是因為,選擇,習慣,受方,三者的關係與如何運作,咱們得好好的把它們看清楚來。
首先來談談什麼是習慣。習慣,即是藉由學習,而一再重複的行為,因為宇宙的法則的一貫性,而自然產出來結果。咱們可以先來做一個小實驗,將你的手機號碼鎖,換一個號碼,然後觀察,新的解鎖會錯了幾次,需要幾天,行為才會完全改為新的號碼輸入。這樣可以觀察自己的覺知狀態,與習慣對自己的影響。信念,也是一種所習而得的慣性。信念常常為觀點定向。
三門問題,即是在挑戰常識上的習慣,而這習慣即會成就「成為受方」的機會大小。
對於三門問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維基百科上的說明 :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8%92%99%E6%8F%90%E9%9C%8D%E7%88%BE%E5%95%8F%E9%A1%8C
在三門提問上可以看到,一個違背常識選擇的習慣,相對於用常識選擇的習慣,會多出一倍成為受方的機會。而這違背常識的選擇習慣,是源於對環境的覺知。
成為受方,增加「受」的機會是調整自己的能量態,即是所謂的「善者果而已」,「處其實而不處其華」。站在結果之上,而不是站在期待之上,期待的感受是一種匱乏的表現,進而引發很多想法,腦子像是拉肚子一樣,一直在往相反的結果餵食能量。這樣會形成「企者不立」的現象。
那麼,一直有想法怎麼辦呢?想法本身沒有對錯的問題。會有問題,是因為以想法在互相打架,而之所以在以想法互相打架,是因為信念的不互容,而信念又跟價值觀有很深的連結,而價值觀跟標籤與自我認同有關。
看清了這樣的千絲萬縷,進而止於「無」而「知足」,把自己丟出去,即可「事無」。
學而後能覺,覺而後能舉,舉而後能與,與世無爭,爭清得靜。
為學日益,學會以「有」界定功能而增益,為道日損,道會生化空間,以「無」運作功能,兩者並進,有無互相生化。
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有」的方式來行「道」,反而會以各式各樣的想法為「意」,動個不停;
以「無」的方式來行「道」,意即可遍佈全域;
用頭腦太多是過,意不知止知足,道即會示禍。
事與願違的災禍是咎,匱乏而想要取得填滿,填滿會招致事與願違。
所以意之所向而知止知足,以此達到足,是長久站在結果之上。
「過」是頭的象形在走。
「咎」,會意各人,表示相違背。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無為而成。」
心神在心神所在的地方,行道而生成萬事萬物。
不執著於眼見之相,才能明白道的運作模式。
心神離開心神的位置越遠,能展現的越少。
所以聖人的心神不離開心神的位置,而行道生成萬事萬物。
視之不見曰夷,是心神,心神以定名生成萬事萬物。
不為了什麼,意不在意處,而得以成就。
第四十八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學事物,是越學越增益,越學越多,會示現更多事物;行道是讓出空間,越讓空間越空,會示現更多空間。以至於不為了什麼,意不在意處。不為了什麼,意不在意處,「無」不是作功的地方,而道以自然而然,有無同出。
行道是以事「無」,如果是事「有」,即是意不止而行道。
第五十章「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兵甲。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人的一生是由生到死。
壽命長的十人有三人。壽命短的十人有三人。意外而死的十人有三人。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太過在意既有的現象。所以以意完整的人,在路上行走不會碰到犀牛猛虎,從軍也不用身披盔甲。犀牛角、虎爪、兵刃都找不到地方施展,都歸於「無」。這是為什麼呢?因爲「無」是這些相的埋葬之所。
「生生之厚」,下ㄧ章有解釋生。是指所見的萬事萬物。「生生」是指在所見的萬事萬物上所衍生出的意。
「善攝生」,是指衍生出來的意要深藏,「洗心退藏於密」。
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朝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三才合一,清靜、知足、合一,整理或與惑的呈現;以「一」來使用工具,使用體處理事情;以事「無」而行道。
感受為何能「知」事情的演化呢?用上面這個方法。
過多以己心有分別立場的行道,分裂出的呈現會減少,體即減少經驗。
意使用過多的分別的工具,或與惑即會分裂而增生不明。
身意之間的互動有過多的方便巧術,人為分支,工巧而不自然,「ㄧ」會分裂分別增生出,特別在「意」,使身生欲的事物。
戒律不斷的制定,也制約不住自己的直奪瞬取的心意。越多越亂。
所以聖人說:
「我」不為了什麼,意不在意處,而保持「無」,身體即能自動生化,
「我」安住於平靜,體自然率直,沒有做作而完整安定。
「我」處理「無」中的事,體自然富足。
「我」將欲歸於「無」,體自然回到原來的樣子。
「國」意中有或,要嗎成咸,要嗎成惑。或與惑。
「伎」是指方術,方法。
第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從事定名跟身體行為,哪一個會示現呢?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見而名。
身體跟展示出的事物、價值觀的生化,是哪ㄧ個讓「吾」產生疑惑呢?
多則惑。吾有身即有患。
得到與失去,哪一個是有害的呢?
夫唯道,善貸且成。有空間才能得到。
所以愛的甚深而執,應理使其不現。
叨叨念念多了,應理示現失去。
意之所向知止而足,不受情緒的影響,不要叨叨唸唸,守正即周行不殆,全而不會停止,可以維持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