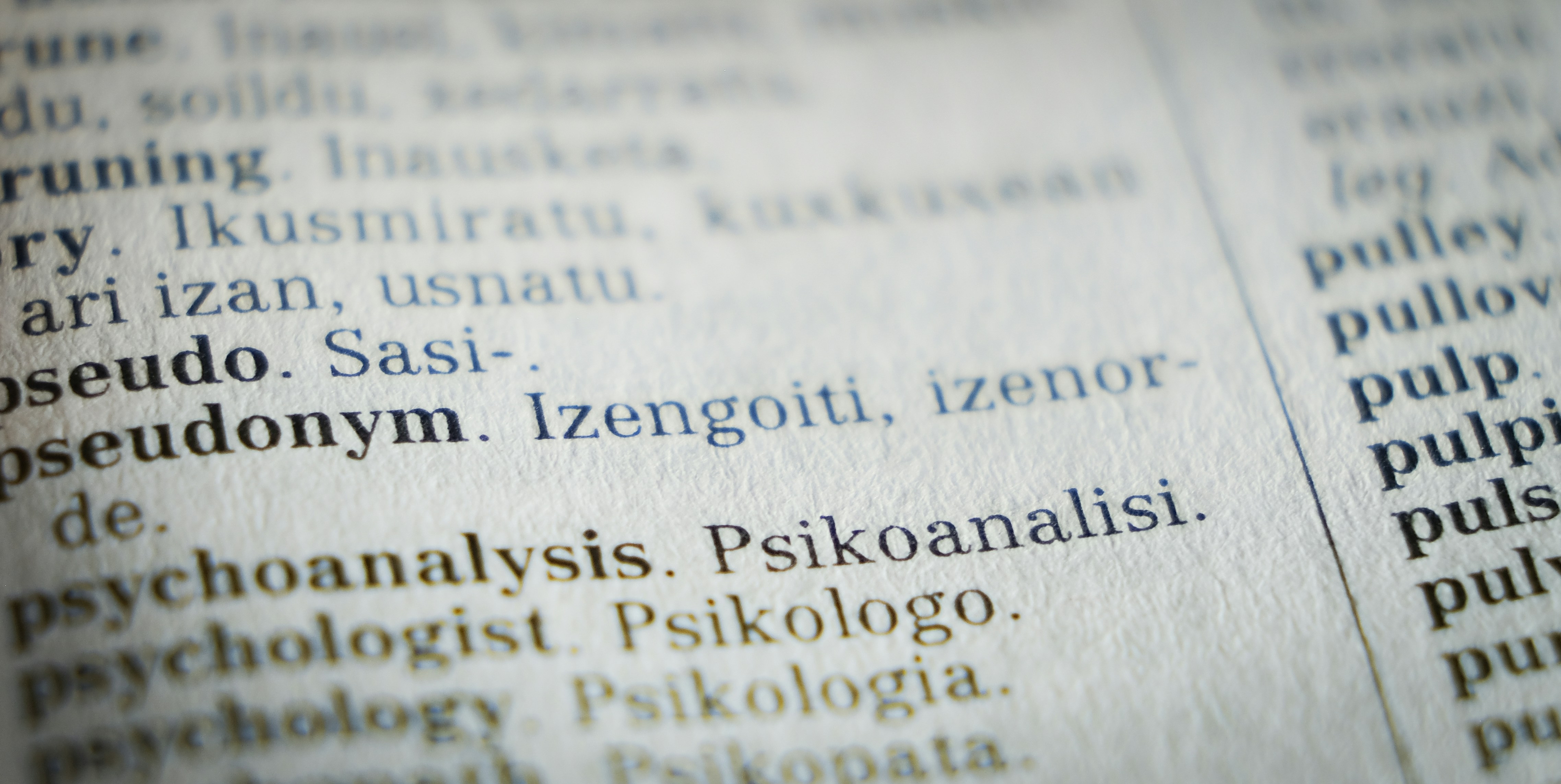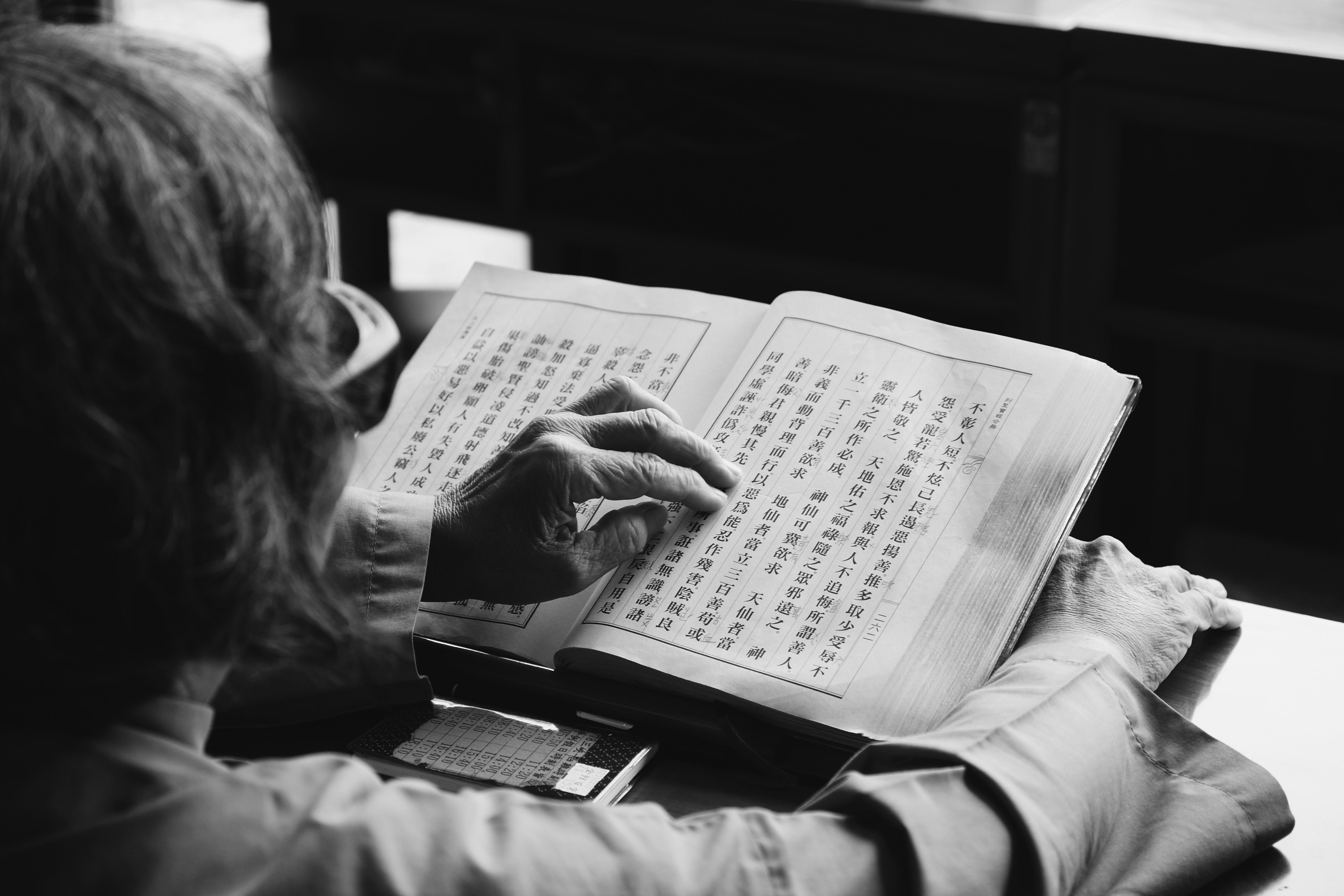在臺灣這篇土地上,有多元的原住民族群,其語言和文化代代相傳,是重要的文化資產。
然而,在歷史長河中,原住民語言曾經面臨過不同時期的困境和挑戰。
本文將梳理自光復初期至今的數個時期,探討臺灣原住民語言教育政策的演變。
從中可以看到,臺灣原住民語言教育政策,從一開始以同化為目的,到後來漸漸注重多元,更開始關注原住民族的主體性。
1945年,臺灣光復後,
語言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標為去日本化,為加速推行國語,允許學校暫時兼用族語教學。
1949年,政府遷臺後,發布「山地教育方針」,推行「說國語運動」,不僅規定教學不得使用母語,更禁止臺灣各族群說母語,包含原住民各族語言、閩南語與客家語。
直到1987年,政治解嚴,鄉土語言復振的風潮才得以發展,然此時期教學、溝通仍以國語為主,瀕危的族語亟需復興。
1995年,教育部修正發布《臺灣地區原住民族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此法便是俗稱「加分制度」的法源依據,於升學考試中,給予原住民學生35% 的優待,其目的在保障原住民學生升學權益,及延續保存原住民族語言文化。
此政策雖給予原住民族更多機會接受教育,然背後的價值觀難免帶著希望原住民融入主流社會的「同化」目的。
1998年,頒布《原住民族教育法》。此法載明:「原住民為原住民族教育之主體,政府應本於多元、平等、自主、尊重之精神,推展原住民族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應以維護民族尊嚴、延續民族命脈、增進民族福祉、促進族群共榮為目的。」
此時期更歷經數度修憲,於修正條文中表明對於「民族意願」的尊重,原住民族於政策中由受左右的客體轉變為具決策權力的主體。
2001年,簽署《聯合國文化多樣性宣言》,並正式將族語納入國民教育的課程。規定國小學生每週有一小時的母語課程,可由閩南、客家、原住民等語言中擇一。國中則依學生意願彈性修習。
學生上課時數非常短,如何與其他科目取得平衡,均衡發展是一大課題。
明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包含聽說讀寫等全面性的語言能力。而該法立法的目的為
「實現歷史正義,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與發展,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原住民族委員會透過族語推廣、傳習、保存與研究等四大面向推動族語復振。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實施後,雖然對於族語教學的品質有所提升,卻讓只會說、不會寫的部落耆老無法教族語,使得族語教育的「語言」面與「文化傳承」面產生斷裂。
而以族語檢定作為升學加分的條件亦受詬病,此舉造成都市原住民,比真正在部落生活的原住民學生通過族語檢定比例更高的現象,足顯城鄉教育資源落差之大。
未來的族語教育政策走向,需要更關注文化傳承,並考量不同地區教育資源的分配,使整體社會環境離真正的平等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