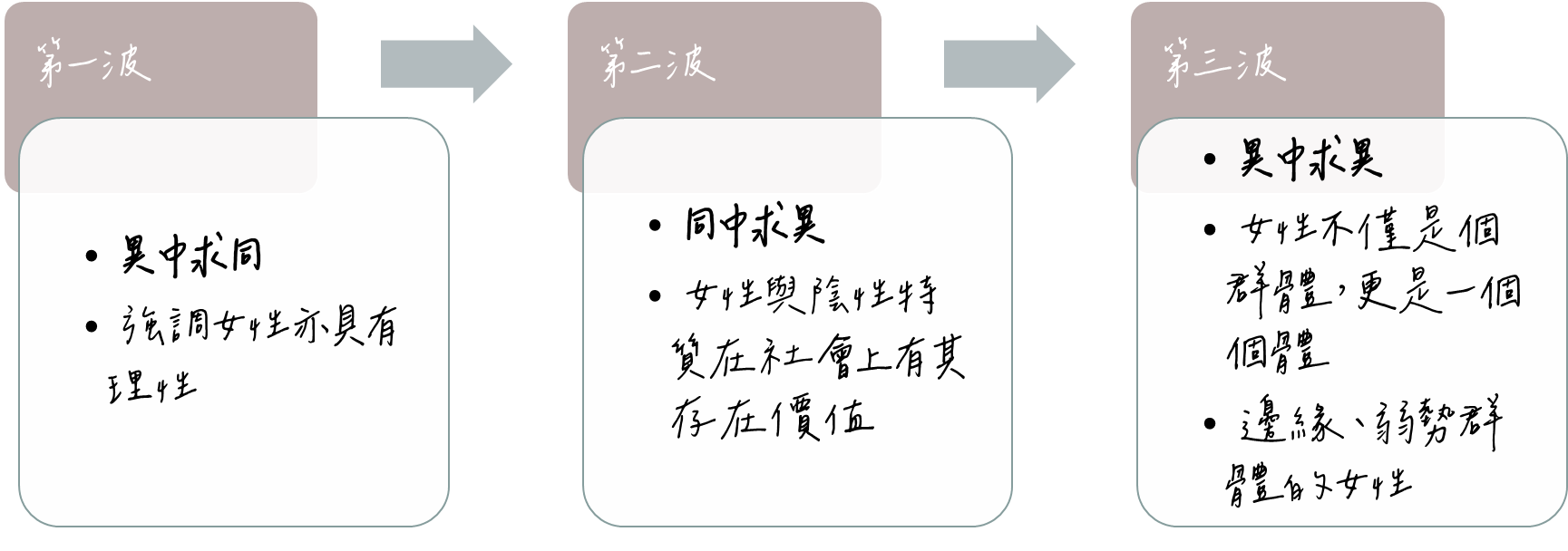此文為對111學年度清大人類所資格考【方法論考題二】的回答,針對Margery Wolf的著作A Thrice-Told Tale的一系列問題。

Margery Wolf (born Jones, September 9, 1933 – April 14, 2017)
Margery Wolf是一位美國人類學家(1933-2017),她於1980年代曾在台灣進行田野調查,特別是關注台灣的家庭結構和性別角色。她的著作The Role of Women in Taiwan中,分析了台灣社會中女性的地位和家庭功能,並探討了現代化對女性角色的影響。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1972))
另外一提,他的丈夫是人類學家 Arthur P. Wolf,他們在冷戰背景下為了研究漢人文化,因此來到臺灣。
介紹完作者,接著進入主題:

Margery Wolf 在A Thrice-Told Tale 一書中,以創意寫作、田野筆記、期刊論文三種文類捕提同一起田野地的事件,請問她對於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與知識生產最核心的論點是什麼?
Margery Wolf 在 A Thrice-Told Tale 透過三種文類描述她於臺灣田野中所發生的同一事件,來回應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對於民族學方法的批評。我會以「責任」和「反身性」(Reflexivity)和作為關鍵詞來理解 Wolf 的核心論點: 人類學者應為其寫作、被書寫的對象負責──Wolf 採取女性主義的立場,雖冒著能否再現他者文化的質疑、殖民主義、作者的威權性,她也要為臺灣女性的處境進行典型人類學的分析書寫。因為透過非實驗性而易讀、採非男性中心提供見解的民族誌,來呈現婦女經驗的多樣性是重要的;於此同時,更要注意田野與書寫過程權力關係的不對等,並永遠保護報導人的權益。
這本書可以看成是 Wolf 作為女性主義人類學者,對於學界中後現代主義批判的回應。我更看到了:有了更豐富人類學養與反思性的 Wolf,因 Hot Spell 回 憶起三十年前被迫離開村落的陳太太。Wolf 必須並想要為陳太太說些什麼,因 此她在後現代的批判書寫與女性主義發聲之間掙扎後,得出了上述的反省── 即如何在肩負女性主義責任的同時,也達成後現代批判所要求的反身性。Wolf 甚至聰明地透過呈現小說、田野筆記、期刊論文三種不同文類,討論各文類在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立場上會遇到的問題之外,實則也透過行動本身揭露了 人類學工作者知識生產的過程,達到讓作者現身、可被檢驗、減少權力壟斷的效果。
跟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觀點有什麼關連?
整本書在各文類章節後皆有 Wolf 的評論,可以看到議題總圍繞在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兩個視角的討論上。根據書中所提供的訊息,James Clifford、 Michael M. J. Fischer、 和 George E. Marcus 幾位重要的後現代主義者,他們對 傳統的人類學寫作提出批判,質疑人類學者們能夠再現他者文化經驗的可能 性,並且對人類學研究過程中的殖民主義實踐提出道德上的疑問。Wolf 認為其實從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來看,對於意識到權力支配這件事情再熟悉不過了,他們比後現代主義者早許多時刻就意識到反身性與權力的問題。女性主義學者們 的知識常被學界認為受其政治訴求影響,因此他們在反思性議題上的價值常被低估。同樣是對於反身性的訴求,後現代主義學者們所提出的意見就受到學界 的看重。對於這樣的落差,Wolf 以其擅長的女性主義立場提供了敏銳的視角: 在學術界當中亦有明顯在性別上權力不對等的問題。
回應方式一:小說
Wolf 以其三個文類展開了對後現代批判的回應。在她引人入勝的小說 Hot Spell 之後,討論後現代批判者所喜愛的「實驗性民族誌」。後現代主義者鼓勵作者呈現出多聲、矛盾的意見,以打破由作者所控制的威權版本,讓讀者承擔更多責任,甚至有時會嘗試以小說文體來呈現。Wolf 認為小說的作法犧牲了人類學作品的可信度,而透過角色呈現多聲實則可能掩蓋了背後藏著的是作者的 敘事。Hot Spell 作為類實驗性民族誌的案例,即是 Wolf 想藉以說明上述問題的發生,她在小說中挪移了時間、給了封閉卻模糊的結尾、虛構了一些互動, 但無法達成某種原先民族誌所能帶來的知識價值與可信度。最終實驗性的文體 會淪為取決作者敘事能力的比賽,而無法提供如 The Woman Who Didn't Become a Shaman 對臺灣乩童信仰、漢人社區中權力關係的分析。
回應方式二:田野筆記
Wolf 對於田野筆記的評論,更佐證了不能只有小說體裁的存在。田野筆記的書寫,讓她能夠檢查故事書寫的不同版本,也發現小說中出現了從未發生過 的行動與事件。雖然的確田野筆記所能紀錄的只不過是事件的吉光片羽,總是部分的、凝固住某刻的行動,但卻對於糾正人類學者記憶有其重要性。Wolf 更舉了例子說明田野筆記的有效性:兩位不同背景的人類學者能夠對同研究區的 田野筆記產生強烈共鳴,並能夠因他人的田野筆記有效幫助對一地的理解。
回應方式三:期刊論文
在 The Woman Who Didn't Become a Shaman ,Wolf 示範了為陳太太的事件提供了社會文化層面的解釋。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都關注都關注讀者、作者、研究課題的選擇三個面相,但兩者作法卻有些不相同。讀者方面,後現代主義者不斷在風格形式上做挑戰,但神秘和晦澀的特色使得讀者亦限於知識菁英,與之相對女性主義者傾向讓更多人閱讀其作品,並以揭露女性處境、多樣性經驗為目標;關於作者,他們都願意探索與報導人協作的可能。然而這可能 會遇到將解釋知識的責任轉移給報導人的問題。是否一定要與被研究者合作, Wolf 於此課題保有彈性的空間;在研究課題選擇上,女性主義者特別會專注於 有利於女性的研究,並採納報導人關切的問題來研究。
總個來說,Wolf 在面對後現代主義質疑民族誌文類對真理有效性,她站在女性主義的基礎上給予堅定的立場──回答道:「我並不為我的書寫臺灣女性道歉」,並認為實驗性民族誌無法處理女性主義人類學者所關切的問題。雖然 要從各種不穩定、無序繁雜的田野紀錄中梳理出民族誌作品,甚至不一定都 「正確」。但 Wolf 以她對 1960 年代臺灣女性遭遇的珍貴資料為證明,她的書 寫將陳太太的磨難化為更具尊嚴的形式,並讓當中的女性們作為有能動的主體 被認真看待。
課堂上關於參與觀察 (DeWalt and DeWalt 2011)、訪談 (Spradley 1979)、田野筆記(Emerson 1995)的討論又能如何幫助我們理解她的材料?
田野筆記
Margery Wolf 這本書最精彩、最能夠提供給人類學學習者反思的,我認為是「田野筆記」的書寫面向。除了第二個文類直接呈現筆記之外,這本書的出現很大程度也要歸功於 Wolf 對資料重新閱讀後產生的刺激:要如何解釋和小說中不一樣之處?面對零散的、分歧的報導人訊息要如何理解?要後現代處理它,或者提出自己的解釋?如何能避免權力上的問題?當然我們最後很清楚 Wolf 選擇了正面接受民族誌文類書寫的限制,並找到書寫的意義。課堂上我們 討論到田野筆記的魔法,就發生於日後閱讀發現其中奧妙的連結與新的詮釋。 Wolf 在事件時隔三十年後重新閱讀了自己的小說與田野筆記,她看出了新的事 物:她發現了陳太太事件被訴說的價值,原本那只是較邊緣的材料;她更加意 識到自己身為美國白人與當地人的權力差異;她後悔沒有多了解助理吳潔對於陳太太事件的看法,以及她如此同情與激動的理由......。
除了「田野筆記」,書中有提到其他的文類:小說、日記、書信......,都是人類學知識生產中的各種紀錄與思考。從 Wolf 對自身文字的評論中,可以看到以上不同文類都是協助她回憶、拼湊、理解、分析,最後生產出人類學作品的重要工具。其中她的小說,並不是田野工作者必要的文類,但 Wolf 卻因小說中對於氣味、濕度、溫度、畫面、情緒、聲響......等細膩的感官描述,將她的回憶能快速的召喚。這裡可以提供的啟示,除了透過深刻的感官描繪幫助田野工作者回憶之外,若作為民族誌書寫者能善用小說的描寫力,更能讓讀者進入所欲勾勒的情境之中。
參與觀察
談及這些親身的感官經驗,就無法不說到「參與觀察」──因為那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所要研究的田野現場。我們無法得知 Margery Wolf 實際上田野的情 況如何,但從書中的文章可以從側面推測她大致的研究情形。若根據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Guide for Fieldworkers 所認為參與觀察的重要元素來評估 Wolf 的田野,她做到了:住在一個情境長達一段時間、能觀察到幽微的訊 息來做分析(比如覺察到吳潔情緒、她的有所保留)、某部分的知情同意(身 為被接待的特殊存在,與外國人臉孔);沒有做到:學習當地語言來對話、積 極參與日常例事與活動、非正式的場合的閒聊。總個來說 Wolf 雖然身處異地, 但由於語言隔閡、身份地位之別,她缺少了更多和當地居民實際的互動機會, 特別是友伴關係的閒聊或一起勞動的過程。這使她只能依賴田野助理吳潔的翻 譯和協助訪談,在參與觀察的光譜上位於偏「被動參與」的類型。要是當年 Wolf 換一種參與的姿態,或許會獲得很不一樣角度的材料。
訪談
從田野筆記中,可以看到 Wolf 高度依賴於吳潔協助的訪談內容。在「訪談」主題的討論中,我們認為田野中的訊息過度仰賴某些報導人的意見是危險的,會受到其視角的限制而導向某種特定結論,更甚者可能無法發展出研究者 位置的評析。雖然 Wolf 最終的訪談對象是多位村民們,然而中間會經過吳潔篩 選要回報什麼答案、選擇問哪些問題等變數,易讓資料的結果受到吳潔很大的 影響,成為了研究上的限制。因此避免資料蒐集上的單一或偏袒,是我們可以 努力的方向。
結論
儘管有許多教戰守則指引田野工作的方向,但田野總是如此的不穩定、充滿各種可能,難以用幾條規則就能獲得預期的結果。唯有實際以肉身直面田野現場、真誠的看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並時刻懷著 Wolf 在此書中所示範的反身性,或許就是對人類學田野工作最有用的建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