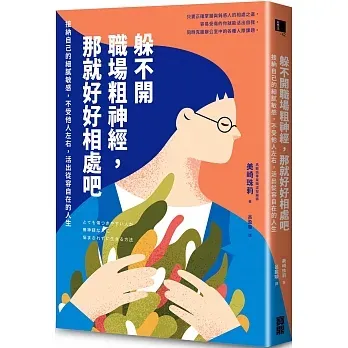|佐鼬|不捨晝夜|07
尖叫聲。
耳裡充斥著尖叫聲。
男人、女人、小孩、老人、親人,一個都不可以放過,這是命令、這是任務,只有他可以做到。
滿手的血腥,黏膩而滾燙,『他們』拖著五花大綁的族人到他面前,可笑的是直到他斬下對方的頭顱,他都十分的迷茫。
為甚麼這些人要死?『為了和平。』聲音從四面八方而來,為他押著族人的『他們』紛紛仰起頭。
『他們』就是自己。
他舉起手中的刀,鮮血四濺,染紅了腳邊的白花,那是甚麼花?是梔子花嗎?
臉上炙熱的究竟血,還是其他多餘的情緒,自己為甚麼要咬著下唇,自己再忍耐甚麼?跟胸口那股幾乎要將它撕裂的疼痛有關係嗎?
既然不知道,那也許不重要吧?跟和平比起來,這些都微不足道吧?
『他們』拖著一對夫妻走到自己面前,他們背上的家徽刺眼的令他難以直視。
為甚麼雙手抖得這麼厲害?
夫妻回頭看了他一眼,眼裡飽含著某種情緒,丈夫的嘴一開一闔的,他明明一個字也沒聽清楚,男人的字字句句卻震的他渾身發麻。
——託付給……誰?他要把誰託付給誰?手中的刀,毫不遲疑的揮下。
在一片血霧之中,他從眼角餘光裡看見遠遠的站了一個小男孩,視線裡全是血,看不清楚。
下一刻他卻看清了,因為『他們』將男孩推到了自己面前。
不只雙手,連身體都在發抖了,為甚麼。
他看不清男孩的表情,甚至有股要蹲下來與他平視、想和他說話的衝動。
可是他不能,刀柄上凹凸的觸感令他有種違和感,似乎在提醒著他甚麼重要的細節。
『為了和平。』聲音又說話了,但『他們』開始扭曲變形,變得和男孩一樣的身形與面貌,用平板的聲音又說:『為了報仇。』
報仇?你為甚麼要報仇?他抹去手上的血汙,扔掉手中的刀,伸手想去扶男孩的雙肩。
男孩卻猝不及防地撞进他怀里。
他低下頭,感覺胸口一陣濕潤,原來男孩手裡還拿著一把匕首,匕首貫穿了他的胸膛。
遍地紅花。
如釋重負的心情令他整個人都放鬆了下來。
『任務完成了。』『他們』語氣歡快地說,又開始變換樣貌,男男女女長幼婦孺,都帶著各村忍者的護額,以他們為中心手舞足蹈,他們就像祭壇上的祭品,人們用他們換取生活的安樂。
『世界和平了。』
他有些懷疑,他們高興的究竟是和平,還是祭壇上的不是他們自己。啊啊,但是為了和平,這樣應該就⋯⋯
——哥哥
他在闔眼前似乎聽到一個微弱的呼喊,幾乎淹沒在一片歡笑聲中,但他還是聽見了,眼前逐漸昏暗下來的畫面又亮了起來。
——哥哥
他看見那個男孩……不,應該說是一個男人,他緊緊抱住自己,單手環在自己腰上,自他臉上落下一串淚珠,晶瑩的水珠碎在他臉上。
——哥哥!不要……
好熱。鼬居然是被熱醒的,這幾年體寒的問題似乎被佐助在不知不覺中調理好了?鼻尖的汗珠在正午的陽光下,在他眼中呈現出一圈光暈,他凝神看了一會兒,抬起手想抹掉時才發現自己身體兩側各被兩個佐助綁住,小佐助像個八爪章魚一樣的捲住他的手臂,佐助就比較含蓄了,掐著他的手腕,不管他用甚麼角度想拔出手腕都聞風不動,被佐助死死的鉗住,更要命的是他身上這一床厚冬被,他自己捲成毛毛蟲,兩個佐助卻睡在棉被之外。
你們倆個,一個是章魚一個是螃蟹嗎。鼬的額角也開始滲汗,難怪自己會被熱醒。
正苦惱著是不是要等他們醒來,還是把其中一個叫醒時,佐助就先醒了,並且放過他有些發疼的手腕。
「醒了?」佐助也發現了鼬有些發紅的臉頰、無奈的表情,自動掀開一邊的被角讓鼬透透氣。
「你們是打算把我熱死嗎?」鼬好氣又好笑的說:「我有體虛到這種程度?」
佐助挑眉道:「你昨天忽然昏倒,還一直發抖,難道不是怕冷的表現嗎?」而且一邊抖還一邊流淚,搞得他頭大的不行,偏偏還叫不醒。
應該是作惡夢了。他昨晚將小佐助安置在床上後,便一直守在鼬身邊,緊握著鼬發顫的手心,直到天微微亮時,鼬終於停止了顫抖,他才慢慢睡去。
「欸?是這樣嗎……」鼬頓時有些尷尬,他後知後覺的發現房間擺設不太一樣,瞬間就回想起昨天在飯館的畫面,太陽穴又開始抽痛,他忍著不伸手按住額頭,問佐助:「那……昨天……」
「沒事了,我帶你們轉移了地點,都處理好了。」鼬半坐起身,決定不問佐助是如『處理』那些村民,就算佐助直接將他們滅口,他也沒有指責的餘地,換作是他怕也是會這麼做吧,但小佐助呢?
「記憶,我消除掉了,他甚麼也不會記得。」包括那些村民,那些忍者,佐助在床上伸了一個懶腰,翻身環住鼬的腰。
鼬眼皮一跳,夢境裡那雙飽含水氣的眼睛與佐助的黑瞳重合,水珠落他在臉上的位置也陣陣發疼,他不禁伸手撫過佐助的眼角,沒摸到濕潤的液體,卻換來佐助有些訝異的目光。
「抱歉。」鼬立刻縮回手,垂下眼皮,夢裡的畫面開始在他腦海重播,刀劍切碎骨肉的觸感是這麼清晰,好像昨天才發生過一樣,那些畫面如此難熬,佐助是否也為此夜夜噩夢?
但佐助現在卻像做了這件事的人不是自己,一次也沒對他提過那晚的事情,即使不像小佐助那般黏人,對他卻也是體貼入微,每一次發病無論多麼輕微,都會被佐助發現,他煎得藥雖然苦的另他頭皮發麻,但他守著藥爐那認真、不容任何差錯的表情,鼬也看在眼裡。
他知道,佐助是認真想幫他治好血繼病,但佐助也說過,自己並非醫療忍者,這些東西也都是他臨時補強的,他也沒有多少把握可以根治,但佐助聽大蛇丸說,至少可以減輕痛苦、延緩發病。
他當時就問了,為甚麼是大蛇丸?佐助一臉神秘的說他很快就會知道了,這讓他想到大蛇丸一直都覬覦著他宇智波族的血統,於是他語重心長的告訴佐助:離那位『前輩』,遠一點。
佐助居然一臉哭笑不得的樣子。
撇開那些不說,他不知道佐助是如何放下那夜往事、花了多少時間平復心情,尤其是在知曉真相後,他是如何讓自己與木葉和解的?至少他認為他是一輩子都放不下的。面對佐助時他多少是有些疏遠,畢竟他們兩人都經歷過那一晚,鼬尚且不知道自己該用哪一種面貌來對待佐助,裝成過去兄長的樣子顯得虛偽,他卻是不忍心對佐助過於冷漠,佐助可是跨越了幾十年的時光,只為了來治好自己的病。
只是,何必呢。
「又道歉。」佐助的眉目有些不悅,他語氣略帶抱怨的說:「實在搞不懂你道歉的原因,我連你做錯了甚麼都沒搞明白。」
「抱歉。」鼬又重複了一次。
「……算了。」佐助伸出兩隻手指,鼬一度以為佐助學自己戳額頭之類的,佐助卻將指尖抵再了他的太陽穴,一股暖流逐漸減緩了鼬的頭痛感,鼬坐直身子不敢亂動,直到佐助放下手。
「累死了,我再睡一下,餓了的話桌上有一些吃的,先墊墊胃吧,等小鬼醒了我們就離開這裡吧。」
「去哪裡?」
「去一些我旅行過的地方。」佐助側過身,說讓鼬可以自主下床,卻再次攬住了鼬的腰,一副忘記自己已經30好幾的模樣,他心安理得地閉上眼,不一會兒便睡熟了。
昨晚為了善後,也是辛苦他了。
鼬猶豫了一會兒,悄悄伸手輕撫佐助如黑色锦缎一样光滑柔软的髮絲。過去這樣的溫柔,他會毫不遲疑地給予他,只是現在這樣的付出對他來說都是那樣珍貴、必須那樣小心翼翼的呵護。
在鼬看不見的地方,佐助悄悄的勾起了唇角,十分滿足的又貼近了鼬幾分,鼬的溫柔令他有股想哭的衝動。
在佐助心中,『家人』一直擁有最崇高的地位,尤其是面對鼬的時候,有時候那份濃烈的情感幾乎超越了一般的家人,他會傾盡全力守護心中最柔軟的那個地方,但對佐助來說,他在未來已經永遠的失去,相比起鼬的小心翼翼,他自己何嘗不是也小心守護著和鼬所剩無幾的時光。
他也必須做好準備,做好讓鼬可以好好活下去的準備,只是到那時候,自己可能已經不復存在了吧,未來的事情,連他也說不準。
--
後來的幾日佐助帶著鼬和小佐助走過了千山萬水,去了所有他覺得美麗的地方、那些他想與鼬分享的景色,有時他也會詢問鼬的意思,想知道他有沒有想去的地方、有沒有想吃的東西。
可惜除了甜食,鼬基本上沒有任何要求,兩個佐助只好勉為其難地將『蒐羅甜點店』這件事規劃進旅行裡。
於是他們乘著佐助的巨鷹,蒐羅了各地的甜食、一起坐在最高的山顶上,捕捉夜空中的流星、在遍地花海裡睡午覺、去看世界上最廣闊的麥田,看一片片金黄的麦子,在微风吹拂下,就像金色海浪一般翻騰、去看碧波粼粼,一望无际的大海……
原本需要數十天腳程的距離,因為有了佐助的通靈獸方便了很多,常常是上午還在草之國的天地橋上看風景,晚上就到了雷之國泡溫泉。這大概是鼬這幾年精神最放鬆的一段時間,生活有佐助在照顧,被認出來的時候,佐助會先一步上去將人放倒,完全輪不到他來操心,佐助也十分滿意鼬很享受這段日子。
「你開心就好了。」佐助這麼說。
「你是跟同伴一起來這些地方的嗎?」
佐助抬頭看著眼前的瀑布,沉默了許久,才說:「不,我自己來的。」帶著你的眼睛一起,這些景色,我只想跟你分享。
天空在瀑布的映襯下是那樣的藍,那么愜意、那么涼爽,小佐助恣意地在瀑布下玩耍,濕淋淋地從水裡撈出一顆光滑黑亮的鵝卵石,衝著他們露出一個燦爛無憂的笑容, 單純而綿長。佐助的眼裡也帶著笑意,不時開口損小佐助幾句,卻透着某種苦思的神情,有种褪尽光泽而黯淡的意味,鼬看著倒是感覺有些眼熟。
接著他想到,這就是他在鏡子裡看見的自己,眼神冷漠疏離,墨黑色的眼仁裡毫無溫度。
說來也是,佐助已經擁有了萬花筒,那麼他的眼睛——鼬張開雙手,接住被瀑布淋的溼答答,朝他撲過來的小佐助。
「哥哥!瀑布下面好涼,一起來玩嘛!」小佐助的身上全是湿的,连着脸上,脖子上,冰涼的溪水顺着额间的发流下,在脸上落下了濕潤的痕迹,在正午陽光的映衬下莹莹地发光。
「他要是下去,今晚又要發燒的,踩踩水就好。」佐助一口否決。小佐助不滿的嘟起嘴,但也明白哥哥確實身體不好,他甩甩身上的水珠,一頭鑽進哥哥懷裡,鼬則拿出毛巾給小佐助擦頭。
看著小佐助單純淘氣的樣子,鼬一想到有一天他會永遠退去這身純潔,在一片肅殺血腥之中變得和他一樣、眼神永遠的死寂時,心裡就不自覺的抽痛,如果這個世界,人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溝通、找到和平的相處之道,那佐助是不是就可以不必面對那些可怕的事情了?
可惜,人類即便見證過多少歷史,還是無法放下貪婪的本性,就像他即便明白錯誤無法挽回、即使知道時空忍術是禁忌,他還是內心渴望佐助可以待久一些、小佐助可以永遠甚麼都不知道,因此他默許了佐助幾乎是濫用的時空忍術、默許了佐助用幻術清除小佐助的記憶。
只因為他內心那不成熟的私慾。他應該讓佐助回去他們的世界的,小佐助還有忍者的學業,佐助是木葉暗部部長,肯定很忙,怎麼能在他身上耽誤如此多時間……
「哥哥怎麼了?」感覺到鼬停下動作,小佐助用腦袋蹭了蹭鼬的下巴。潮濕麻癢的觸感將鼬喚醒,他放下毛巾,緊緊抱住了小佐助。
如果可以……如果可以……希望你……
鼬輕微的嘆了一口氣,他究竟希望佐助成長強大,還是希望他是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但他知道,時間到了。
--
沒想到如此冰天雪地的雪之國,也會有如此熱鬧的慶典,更令鼬驚訝的是,擔任嚮導的佐助竟也是一臉的茫然。
「我之前來的時候,雪之國並沒有這種慶典。」佐助鎮定地解釋道。
而且在暴風雪裡到底要怎麼舉辦慶典阿!?連走路都是問題好嗎!佐助的困惑不比其餘兩人少,自己好歹也曾在雪之國停留過一兩年,怎麼就沒見附近鄰居邀請自己去參加甚麼慶典?他卻沒想過自己那冰山般的表情、剛結束第四次忍界大戰後尚未消散的肅殺之氣,人家都還沒跟他說上話就被嚇跑了,就算沒聽過『宇智波佐助』響噹噹的名號,從佐助的氣場也看得出是個惹不起的角色,佐助定義中所謂的鄰居,也只是剛好住在隔壁,每天出入難免會見面而已,佐助可是連招呼都不打的,人家就算有心也沒機會跟來去匆匆的佐助告知慶典的消息。
不過現在至少是見識到了,而且跟最想一起分享這慶典的人在一起。
佐助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冬衣,將小佐助和鼬裹成兩坨行走的雪人,才滿意地將剩下的圍巾毛帽塞回卷軸裡,不等佐助開口放行,小佐助就被敲鑼打鼓的聲音吸引過去,一頭栽進了人群,還不忘回頭喊兩人跟上。
臭小鬼,只知道玩。佐助瞇了瞇眼,起身打算追上去,以免小佐助被人群沖散走失。
「佐助,你不也多穿些嗎?」佐助回頭,看見一個矮了他一顆頭的雪人正仰著頭,一副老成持重的皺眉道:「你這樣會感冒。」
「不會,我不冷。」況且他住在雪之國的那段時間也是這麼穿的:薄衫、高領、萬年風衣。
鼬看著佐助逐漸凍紅了的鼻頭,默默地解下了圍巾。
難以想像,這麼一個大人居然是這樣照顧自己的,他八歲之後的日子到底是怎麼過的,鼬不敢想。
「幹甚麼,戴好。」佐助急忙要搶過圍巾幫鼬戴回去。
「聽話,我就不管你沒穿外套甚麼的了,至少圍巾戴上。」
鼬難得嚴肅了些,佐助立刻乖乖地動都不敢動,鼬很順利的將被他戴的暖呼呼的圍巾裹在佐助的脖子上,還需要稍微墊高腳尖。
佐助看著鼬湊近他眼前,見他斯文秀雅,一絲不苟地繫圍巾,髮梢上沾了些皑皑霜雪,嘴角淺淺噙著一抹笑,似乎連鼬自已也沒有發現自己愉悅的心情,佐助頓時沉迷在鼬的淺笑中,不舍得把视线从他脸上挪开,直到鼬自覺有些靠得太近而退開,才戀戀不捨的收斂視線。
「我們、去找佐助吧。」鼬不自然的錯開視線,在人群中找尋小佐助的影子。「恩。」雖然有些遺憾,但他也不想讓鼬尷尬,而且他已經決定——
手心猝不及防的被另一個溫暖的掌心握住,佐助一僵,低下頭看見一隻指節分明的手輕輕牽住了他唯一的那隻手。「走吧。」鼬拉著佐助向前走,獨露出有些發紅的耳根。
佐助反手握緊了比記憶中還小的手掌——也許是自己的手掌變大了——心中的暖意將他填的滿滿的,幾乎要從他的嘴角溢了出來,他抿緊下唇,避免自己笑得像個傻子,引來路人的側目。
「哥哥哥哥!」小佐助興奮地拉著鼬的手說:「剛剛我聽店家老闆說,晚上會有煙火喔!」
佐助抬頭看看飄雪的天空,有些懷疑道:「這種天氣,你確定?」
小佐助急道:「你不相信我!?」
鼬無奈地一手牽著一個,看著兩人在自己面前鬥嘴。
好在旁邊攤位老闆聽見他們的爭吵聲,笑著解釋:「幾位是外地來的吧?雪之國的煙花祭典特別挑在了最容易下雪的季節,過去是家家戶戶都會準備特製的煙花,哪戶人家的煙火能順利在大雪裡放出圖案,那戶人家就會受到祝福,代表今年無論有多艱困都可以順利度過,後來慢慢演變成祭典晚會,如果煙花能在半夜12點前順利燃放,對著煙花許願便可以達成願望!」
「沒想到雪之國會有這樣的活動,過去從未聽說過呢!」也曾經在雪之國出任務的鼬對這樣的慶典也感到十分新鮮,通常祭典都會舉辦在溫暖的夏季或春季,雪之國偏偏喜歡辦在漫天飛雪的冬天,越是寒冷他們越是起勁。
「可不是嗎!過去雪之國到處都有這樣的慶典,後來逐漸沒落,只有我們這種偏遠小村庄還保留這樣的習俗。」這位老闆的眉毛鬍子都花白了。但臉膛仍是紫紅色的,比佐助三人還來的神采奕奕,「我們國家長年都處在這樣冰天雪地裡面,生活相較其他國家來的艱困,要在這種地方求生存,當然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和團結,天氣越糟糕,我們越是要樂觀面對,你說是吧,小哥!」
鼬嘴角彎彎地牽挂着一抹笑容,買下三枝糖葫蘆,強迫兩個佐助一人一支。
當佐助們正苦著臉,考慮如何下口時,鼬順便向老闆打聽該去哪裡觀看煙火視野最好。
「冒昧問一下,三位應該是家人吧?」家人。這樣的詞彙輕巧的刺進鼬的心裡,他尚未想到如何答覆,身後有兩個聲音異口同聲道:「當然!」
老闆顯然被兩人的反應逗樂了,他朝東面只了一個方向說:「看見那邊的小山丘沒有,從那裏可以看見最完整的煙火,這可是我們當地人的秘密景點,記得早點去佔位子,再晚些那兒就會被占滿了!」
「多謝。」佐助頷首表達謝意。
「不會不會,大哥你一個人帶兩個孩子出門辛苦了,當爸爸著實不容易啊!」「多謝您了,我們趕緊去佔位子了。」
不等兩個佐助發作,鼬便捲起袖子把兩人拖走。
「誰是爸爸!」我明明是弟弟!
「誰是大叔的小孩!」誰要做他小孩⋯⋯不對、他就是我啊!兩個佐助氣得一口咬碎糖葫蘆。
倒是鼬心情頗好的樣子,臉上的笑容自始至終沒有消退,看見甜食就掏錢,沒錢就望著佐助,害佐助有種自已真的當爹的錯覺,比自己有個女兒還真實。
三人吃飽喝足後便往山丘前進,憑藉忍足和佐助霸道的氣場,三人很快的排除異己,得到一個視野完美的座位,佐助還貼心地準備了地毯,小佐助趁機偷偷問鼬:那個佐助的卷軸是不是甚麼神奇的寶貝,要甚麼有甚麼,容量奇大。
不,他只是比較高端的卷軸而已。鼬拍掉小佐助髮上的白雪,眼中濃濃的是一層笑意。
佐助升起一堆篝火,召喚出巨鷹給他們擋風雪,三人依畏在火邊,等待煙火。
雪花漫天卷地落下来,犹如鹅毛一般,纷纷飛扬。大地一片雪白,好象整个世界都是银白色的,风雪中夹杂着村民的歡笑聲,喜悅的氣氛在這樣寒冷的國度,竟是如此和諧。
風雪中,有人舉起橫木,撞響祭典中心那沐浴了千年滄桑的銅鐘,悠悠的迴響傳向廣袤的天宇。
「要開始了!」小佐助那张与鼬极其相似的面容上挂着兴奋地红晕,在鼬懷裡扭動著身子,鼬只是輕笑著換了一個舒服的姿勢,靠在佐助身側。
随着一声突如其来的响声,一团彩色的光芒快速上升着,留下一线灰色的烟雾,傾刻间便把夜空點亮,变成了烟花的海洋,五颜六色的大球重叠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又变成一颗颗宝石镶嵌在夜幕中,最后,渐渐变成一道星光瀑布慢慢地坠落下来,流光溢彩。
烟花姹紫嫣红 , 转瞬即逝犹,昙花一现,卻叫人如痴如醉。
佐助旅行過世界,也參加過不少特殊的民俗慶典,卻未曾有過如此感動的情緒,他看著身邊被光芒照亮的兩個孩子,他們的笑容瞬間填滿了他的心口,多希望他們永遠可以有這麼幸福的笑容,這一個月轉瞬即逝的時間,在這之後,他便不能再像這樣保護他們,這之後所有的困難,都必須自己熬過去,但是⋯⋯
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佐助?」注意到視線的鼬撇過頭,關切地問:「怎麼了?」
「沒事。」佐助回過頭,望著天空,想著方才看見的笑容。
-
煙花活動直熱鬧到了深夜,不只是煙火的施放,還有許多村民的同樂活動,家家戶戶拿出自己釀的酒和食物,圍著溝火唱歌跳舞,面對外人他們也十分好客,好酒好菜的招待像佐助等這樣的外地旅人。
小佐助原本還特別興奮,甚麼好玩都想去參一腳,但很快就因為到了睡覺時間昏昏沉沉了起來,最後還是佐助拎起小佐助,帶著鼬先行向村民告別。
「是個有趣的地方呢!」鼬難得分享了心得,還偷偷揉了一把被佐助抱在懷裡的小佐助。
有機會再來吧。佐助將這句話含在嘴裡,吐出來的卻是:「我們該走了。」
鼬愣了一會兒,一下子沒搞懂佐助的意思,但也很快明白了過來。
兩人一時相對無語。
佐助不知道該如何道別。
鼬還沒做好心理準備。
兩人在風雪中沉默良久,最後還是鼬先開口了:「謝謝你,佐助。」
佐助愣愣的看着眼含笑意的兄长,有些不知所措,想著也許該說些安慰的話,但他並不是善於言詞的人,比起用言語對談,他更擅長用拳頭說話,但眼前的人第一個他捨不得打,要是真的打起來,自己也沒有太大的勝算打的贏兄長⋯⋯
「這幾一個月對我來說就像夢一樣,比做夢還夢幻,我還想是不是我的想像力太豐富了,」那张风雪里坚毅的面容,目光永远都像是大雪弥漫的寂静旷野,遙遠而虛幻,「但這樣的佐助,卻是那樣真實呢。」
「鼬⋯⋯」
「我想再抱一下佐助,可以嗎?」
「⋯⋯好。」佐助眼見鼬不打算說下去,便將抱在懷裡的小佐助遞了出去。
接著他卻被緊緊抱住了,鼬連著小佐助將他一起抱住,對方身上的溫度讓他渾身發燙,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心仿佛要飞起来一样在胸膛里乱撞。
「⋯⋯佐助,我知道我對你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傷害,未來你也許感到很孤獨,想著要追逐我的影子,但我希望你可以知道⋯⋯」鼬收緊了雙臂,將頭塞進佐助的頸肩,「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著,過你想要的生活,無論你變成甚麼樣子,你都是我唯一的弟弟。」
我這輩子最愛的人。
「⋯⋯我知道。」
你也是。
兩人貪戀著彼此身上的起息和溫度,中間還夾著一個小佐助,佐助雖然很想隨手把人丟一邊去,好好跟鼬做道別,但是他這一丟,鼬肯定是要回頭去撿的,他不想浪費剩下的這幾分鐘。
「⋯⋯哥哥,」佐助看不見鼬的表情,但他自己的眼眶已經開始發酸了,難以割捨的情緒正逐漸將他溶解,「好好照顧自己。」
「恩。」鼬將下顎靠在佐助肩頭,两眼凝视着远方,任泪水流到嘴边,嚐著酸涩的味道。
最終也是鼬先放開了手,他緩緩揚起頭,對上佐助的視線。
佐助的眼腈,像黑色的玻璃球浸在清水里,飽含著哀傷的意味,瞳仁逐漸分離出三顆勾玉,接著凝結成一顆五芒星,五芒星中還有一個鐮刀形狀的萬花筒,鼬認出來,那是自己的萬花筒。
自己還算是有好好遵守諾言的吧。在失去意識前,鼬這麼想著。
這次的夢裡沒有那些血腥可怕的畫面,是他們三個人一起看煙火的幸福畫面,在夢裡佐助不是獨臂,他伸出雙臂,把他紧紧拥入怀里,佐助的擁抱溫暖的令他窒息,佐助似乎在他耳邊喃喃說了句甚麼話,但所有言語都被他們身後煙火綻放的巨響淹沒,他沒有機會向佐助問清楚。
——佐助?
-
他猛然睜開雙眼,半晌後,雙眼才漸漸清明起來。
這是?
鼬有些茫然地從床上坐起來,看著熟悉的旅館,他想起來這是他幾日前與鬼鮫分別後修整的地方,那時他似乎血繼病發作的厲害,咳嗽頭痛甚麼的⋯⋯
他揉揉眉心,發現那些症狀好像一夜間消失無蹤了⋯⋯他這到底是睡了多久,腦海裡似乎有一部分是空白的,任鼬怎麼回想都記不起這幾天究竟都做了些甚麼?是睡了好幾天嗎?是不是中途吃了甚麼藥之類的?
⋯⋯想不起來。照理來說這種記憶空白的情況,應該讓他提起警戒,這也許是某個忍者趁他昏迷之時對他不利,但他卻無法提起這份警覺心,好像睡了這幾天,把他的警戒感都睡迷糊了。
但他似乎,做了一個很長的夢?而且似乎是好夢?
他決定放棄糾結這件事情,但這也表示此地不宜久留,他立刻收拾了東西,下樓退房。
一問樓下的掌櫃,自己居然在這裡住了足足有一個月,他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停留超過兩個禮拜,這次住了一個月,自己卻甚麼也不記得。
鼬暗暗有些心驚,但潛意識似乎並不覺得是甚麼大事,他一邊絞盡腦汁想回憶初一些蛛絲馬跡,一邊穿過旅館的前廳。
旅館一樓還兼做了小茶館,隔壁有個很熱門的飯館,到了用餐時間經常是人滿為患,他不能去人太多的地方,於是撿了旁邊的小路出去。
茶館零零散散的做了幾個客人,其中一個渾身包得密不通風的男人吸引了他的注意,男人的瀏海遮住了半邊的臉,但仍可看得出有些銳利的五官,俊雅劍眉下的黑眼珠如一泓清水,里边似乎隐藏着无穷的心事。
鼬不自覺的多看了男人幾眼,男人也看見了他,鼬的雙腳立刻就不受控制的挑了靠近男人的路走,他有些吶悶自己的行為,但眼睛都對上了,現在掉頭走別的路又顯的心虛,他倒要看看這男人有甚麼古怪,也許跟他這幾天的『失憶』有關。
「你好。」
「⋯⋯你好。」真的走到男人面前時,男人反而有些手足無措,話都含在嘴裡說不清。
「先生是旅人嗎?」鼬掃過男人的裝束,猜測是途經此處的自由忍者。
「⋯⋯姑且算是吧。」男人搓著披風的衣角,鼬竟是覺得這樣的行為特別熟悉。
「這位小哥是忍者吧,你打算去哪裡。」鼬輕輕瞥了男人一眼,淡淡地說:「與你無關。」語氣裡頗有警告的意味。
男人立刻就閉嘴了,鼬也不打算繼續在此地浪費時間,男人看起來對他沒有惡意,想來也不是他以為的那樣,與他的『失憶』無關。
「好好照顧自己。」
輕輕一句話,竟是讓鼬定再了原地,動彈不得。
那些夢裡的畫面頓時在腦海裡炸了開來,雪國的煙火、佐助在瀑布下戲水的身影、佐助的獨臂、佐助憂慮的眼光,所有夢境同時湧上心頭,他的意識一時抓不準那些是現實,那些是夢境。
男人的面容與夢裡的佐助重合了。
如夢似幻。
「⋯⋯佐⋯⋯助?」他瞬間意識到了甚麼,猛地回過頭想在找那名男子時,座位上只剩下一盞未涼的茶,甚麼人也沒有。
——怀念那些與你在一起的日子,那些烙印在心底的记忆,一輩子也无法忘懷,也许我们無法再见面,也许那段深刻的情感只能成为过去,但你却是我最感动的牵掛,即使意識有可能永遠消散,我也想為你放手一搏。
——就像你說的,我不會在追逐你的影子,我要去找尋自己想要的生活,那麼這次,我要讓你不再只是影子,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