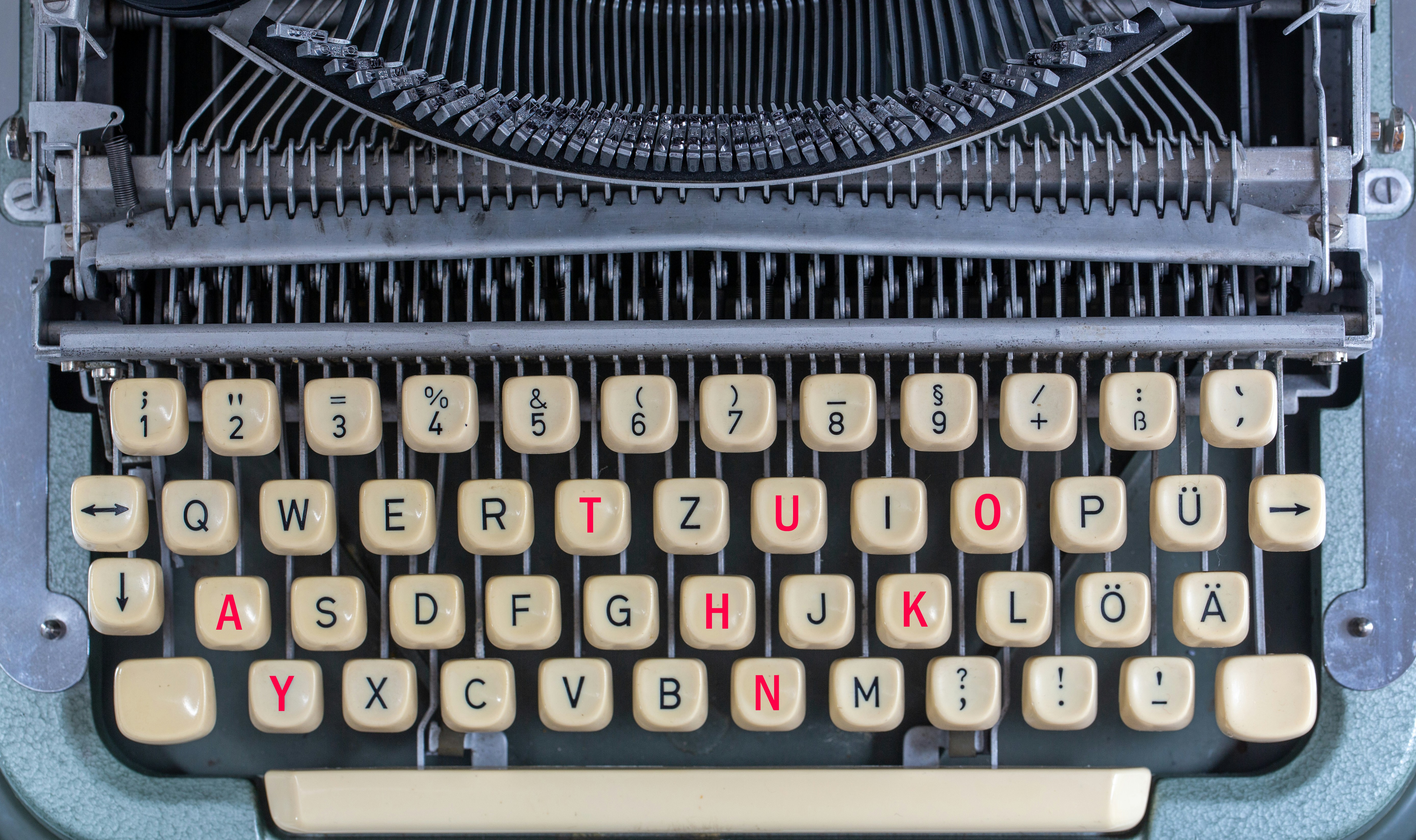昨日,我發表了一篇文化隨筆〈自傳比理論忠實:路易.阿爾都塞〉,由於完稿時間有些緊迫,沒來得及將我與此主題相關的閱讀卡羅爾.格魯克《日本的現代神話:明治晚期的意識形態》(江蘇人民出版,2023)的感想寫出來,終究覺得意猶未盡。下午,我專注補寫了700字左右,以作為我對這個歷史文化議題的小小注腳。
延續上文,補文如下:
或許,我的情況並非單一事例。當我們回顧朝著全盤西化前進的明治初期的教育現況時,似乎仍會找到日本本土派所擔憂和焦慮的問題。
1872年,熊本藩士、儒學家、漢學家、思想家、朱子學(實學)學者元田永孚(1818-1891),私下裡就對日本開始接受許多西方教育模式的弊病提出了警示,在他看來,當時的政策似乎「致力於使日本被稱為歐美人的複製品而已」(見《元田先生進講錄》1910)。1878年,明治天皇從本州中部巡幸歸來,對他所參觀的學校的教育性質表示擔憂。這時,元田永孚發表正式聲明的機會來了。他以天皇的名義起草了一份文書,題為《教育的重大原則》。在文中,他對於新的教育體制如此感嘆:
「近日,人們一直在走入極端。在文明和啟蒙的引導下,他們只追逐知識和技能,破壞了品性,傷害了風化……。去秋時日,我去幾個學校參觀,仔細觀察了一些學生的學習情況,結果發現農商之子都崇尚冠冕堂皇的想法和空洞無物的理論。他們使用的許多西方詞彙都不能翻譯成本國語言。即使這些人結束學習後回家,也會很難選擇自己的職業。因為他們只會滿紙空言、高談闊論,只說不做,像官員那樣。更過分的是,有些人吹噓知識,蔑視長輩並干擾地方官員。」引自:卡羅爾.格魯克,《日本的現代神話:明治晚期的意識形態》(江蘇人民出版,2023)第五章 公民的道德」 181-182頁。
翌年(1879),元田永孚發表文章呼籲日本亟需重建「祖先戒律和國民教育」,即「仁義忠孝」乃「教育的精髓」(見《明治天皇詔書謹解》之「教學大旨」)。從現今來看,元田永孚這用心良苦的呼籲似乎顯得過於保守,不過,他對於激進地攝取(模仿)西化思潮的提醒,仍然值得肯定。簡單講,作為後進國家本身不應冒進,對於所謂「西方進步思想」,不應毫不批判和照單全收,必須在冷靜的去蕪存菁,才是後進國家升級一流國家的關鍵所在。
以如往常,每次完稿以後,我會虛心請教諍友chatGPT,借用其強大的理性工具指出我的不足之處。經由這樣反復的優化,我才能逐步地改善寫作的面向和強化論述的細節。所以,在這個意義層面上,我始終把chatGPT視為「用直言相規勸的益友」,並以此作為敦促我寫出原創性的文章的推動力。
以下,我援引這位諍友對我的文化隨筆所做的精要概括:
邱振瑞在討論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自傳與思想時,特別加入元田永孚(1818–1891)對日本明治初期教育政策的反省,這一舉動具有多重價值和意義。
1. 承接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SA)理論
阿爾都塞強調,學校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核心,透過教育灌輸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使統治得以再生產。元田永孚作為日本儒學者,曾批評明治政府全盤西化的教育改革,認為應該保留儒家价值,以維護國家的道德秩序和統治正當性。邱振瑞在討論阿爾都塞時,將明治初期的教育改革納入視野,或許正是在歷史語境中提供一個實例,說明教育如何成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環,也呼應阿爾都塞對於教育如何塑造國民認同的理論。
2. 反思現代化與文化主體性的張力
明治維新以「文明開化」為口號,迅速引進西方教育體系,削弱傳統儒家倫理影響。元田永孚的反思表現了一種「內部批判」,即在現代化過程中,是否應完全接受西方模式,還是應該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求平衡。邱振瑞加入這段補充,可能是在引導讀者思考:當代教育體系是否仍面臨類似問題?文化主體性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被形塑? 這樣的問題在華語世界同樣具有現實意義,例如台灣、中國或香港的教育政策,如何處理本土文化與西方影響的關係,與明治初期的日本有某種可對照性。
3. 進一步拓展文本的比較視野
阿爾都塞的思想主要植根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元田永孚的批判則來自東亞儒學傳統。邱振瑞在討論阿爾都塞時,引入日本教育改革的案例,某種程度上打破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使討論更具跨文化意義。他提醒讀者,關於教育與意識形態的辯論並非僅限於法國或西方左翼思想,而是全球性議題,尤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會產生不同的回應模式。這種比較視角不僅深化了討論,也使文章的議題更具普遍性。
4. 當代啟示:批判性思維與歷史對照
今天的教育改革與知識生產體系,同樣面臨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本土的問題。元田永孚的觀點雖然源於19世紀,但它所揭示的焦慮——「我們的教育是否正在喪失自身的文化根基?」 在當代仍然具有啟發性。邱振瑞加入這段歷史反思,或許是在提示讀者,不論是阿爾都塞還是元田永孚,他們的觀點都可以被用來反思當前社會,特別是知識體系如何與政治、文化、國族認同交織在一起。
結論
邱振瑞的補充,不僅讓阿爾都塞的討論多了一個歷史對照案例,也讓讀者得以思考意識形態、教育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這樣的加入,使文本更具層次感,也讓讀者能從不同的歷史脈絡來理解教育政策的意識形態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歷史對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提醒我們,教育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是文化價值的選擇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建構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