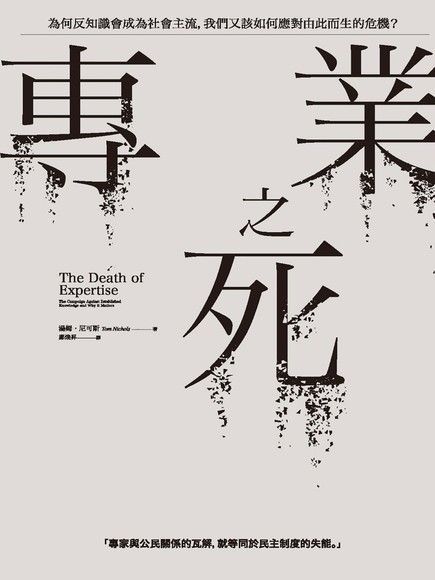本文首刊於Readmoo閱讀最前線,特此致謝
連結:https://news.readmoo.com/2024/07/16/240716-the-polymath/
博學者走向何方?這本《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是我近來讀到最精鍊的、目標明確、廣泛的蒐集並列舉具代表性的資料的研究著作之一。本書開頭就說得很清晰:作者柏克(Peter Burke)的目標不是要蒐集盡歷史上每一個或大多數的「博學者」的故事;而是要把目光聚焦在「時代」:什麼樣的時代氛圍,什麼樣的環境,有利於孕育出「博學者」的存在?或者,相反的,什麼樣的時代氛圍(如今天),容易讓人們傾向於批評博學者「貪多務得,不務正業」?[1]在我們這樣的時代,博學者常常被批評為「浪費了很多時間在瞭解非本行的知識,卻無法專注的在一個領域中做出成績」。而此時代的因素對博學者的影響,正是這本《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試著去解答的問題。
顯然,會問出這樣的問題,很可能已經不只是一種歷史的興趣,而是關於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包含了作者對於我們自己所生存的這個時代、也就是「現代」的關懷。
現代:已專業化的時代,在專家與通才之間「猶疑」的時代
讓我們從「現代」說起。
我們今天的這個時代,是個充滿對立、但也相對多元的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發聲的機會;不一定有某種觀點能贏得大多數人同意。大多數人所「贊同」的觀點,背後也未必有什麼道理,只能用人數的統計去摸索它。
這便是這個時代的缺點:「重量不重質」;人們不太在乎,或不願深想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而只在乎別人怎麼想(所謂的「風向」)。但這個時代的優點也在於:沒有一個定於一尊的最高觀點;當有不同意見的人,想要追求更高的真理時,(一般來說)沒有人會去阻止他。大多數合法的人,都是各信自己的宗教,各過自己的生活就罷。
而我們再把這樣的時代處境,帶回「博學者」的這個問題來看:我們更會看到這個時代多元觀點的特別之處。「今天」的意見是:在要培育出「專家」或是「通才」的問題中,沒有一個主流的意見;或者說,「主流」的意見可能不是固定不動的、講得出某個確切的道理的,也許今天大多數人投票支持「通才教育」,過個幾天,因為某些偶然的、沒有決定性的新聞報導,同一批人又轉為投「專業教育」一票。不過,若是某個人想要成為專家或是通才,我們也會認為那是各自的選擇,而不會有人去阻止他(或許他的親朋好友除外)。
但過去,不論是古典或是近代,都並不是這個樣子。
「通才」的時代:古典時期
在近代,尤其是19世紀末-20世紀中期這段期間,人們幾乎是一面倒的批評「博學者」沒有在一個特定的領域做出成績,主張要將各個學科專業化、領域化。這樣的想法也延續到今天,現在仍然有很多偏向於培育「專家」、而誤以為「通才」往往對社會貢獻不大的想法和心態存在。
相反的,文藝復興以降一直到17世紀結束,人們則難以想像不是「通才」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只有一個可能的形象,那就是通才。被後來的史家歸類於某個特定領域的「專家」的學者,在當時,往往對於許多領域都有廣泛的研究(至於研究的精不精彩,準不準確;那又是另一回事了)。這是決定於這幾百年來人們的希臘式教育理念:掌握比較全面的、關於「人」的各方面知識,也就是所謂「自由七藝」(Artes liberales,另一個常見的譯名為「博雅教育」)的學者,才能夠成為一個更整全的人。[2]如果我們做一個跨文化的對比,我們會發現中國儒家傳統也要求「君子」要能夠瞭解「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並且這同樣也是為了要培育出一個整全的人。[3]看來這是在不同文化中,古典教育理念的相通之處。
這將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瞭解在過去的社會中,有什麼是超越於文化差異,讓人們都希望「通才」誕生的理由;以及那個理由,在今天還適不適用。
不過,通才的全盛時期卻斷在19世紀末。
專家的興起:知識爆炸
本書作者柏克說了一句很中肯的話:
面對知識爆炸,當時的主要回應便是專門化,以減少需要精通的資訊量。專門化可說是一種防衛機制,對抗資訊氾濫的一堵堤防。
[4]這句簡潔精要的話,便告訴了我們今天身處的這個「專業化時代」是怎麼到來的。「專業化」首先是人們對於「知識爆炸」的回應。因為知識太多了,一個人往往無法再瞭解大多數的知識;於是,讓一個人在某個特定的學科中,完整的瞭解、做出新的成績,似乎才是知識分子報效社會最好的方式。
造成知識爆炸的原因,最主要的兩個便是:一開始是印刷術的發明;再者,是電腦在近一百年內的誕生與廣泛運用。於是,「專業化」隨著「知識爆炸」,在我們今天的這個電腦時代達到高峰。
結語
以上是對於「通才」與「專家」之爭,其背後的歷史背景做一個簡短的回顧。至於更細膩、更詳盡的內容,當然還是要回到我們這本(中譯本)約400頁的《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來閱讀。不過,關於我們今天應該像古典一樣選擇「通才」,或是像近代一樣選擇「專家」呢?這可能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跨領域」是近幾年來高等教育興起的一種方式,希望能夠兼收「通才」與「專家」的長處,讓學術研究能做得既全面、又細緻。但我個人以為那還是太偏向「高等」的作法,未必是每個人的時間、財力、和天資條件所能夠負荷的。如果照古典的理想,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整全」的人,那我們應該可以找出一個更普遍適用的辦法。
註解:
[1]彼得.柏克著,賴盈滿譯:《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通才是如何煉成的?從達文西到桑塔格,文藝復興到當代最詳盡的知識人文化史》(臺北:麥田出版,2022年),頁18。
[2]彼得.柏克著,賴盈滿譯:《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通才是如何煉成的?從達文西到桑塔格,文藝復興到當代最詳盡的知識人文化史》,頁49。
[3]吳經熊:〈孔子內心生活的三部曲〉,《內心悅樂之泉源》(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年),頁67。不過吳經熊此文僅以「詩、禮、樂」作為舉例,並沒有直接提及六藝。
[4]彼得.柏克著,賴盈滿譯:《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通才是如何煉成的?從達文西到桑塔格,文藝復興到當代最詳盡的知識人文化史》,頁204。
2024/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