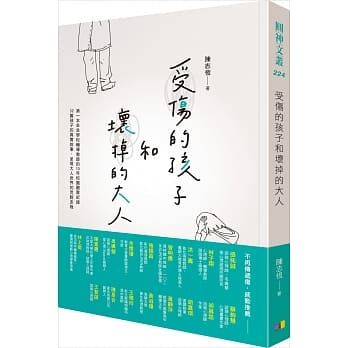為什麼有些孩子被強力規定的時候可以有很好的「表現」,但在沒有強力規定的時空裡,卻像一攤爛泥或總是做出相反的事情?這並不見得是因為那個小孩需要被規定,反而可能是因為「過多的規定」,讓他錯過下決定的經驗,而在日後無法面對複雜的、需要頻繁下決定的世界。

盧果、盧駿逸提供
最近我們光合自學團(A.K.A. 黑龍騎士團)開始運作,幾個從小看著長大的高年級小孩選我當導師,我跟他們約定每週聚會一次,協助他們規劃安排學習計畫。
其中一位孩子說他想要書寫,我們討論一陣子之後,他決定要寫自己的自學生活,向大眾(?)介紹自學這種事情,也說一些他自己的想法跟感受。我們討論了幾個讓他更有動力的作法,最後選擇用FB粉絲頁來騙一些讚,作為持續寫作的動力之一。
但只有粉絲頁的回饋大概是不夠的。做為導師,我也在想要怎麼增加其他的動機,構成一個覆蓋整個日常生活的「劇本」,讓他更有動力去做這件他本來就想要做的事情。我目前有兩個打算。
一個是每週的聚會時間,我可以陪在他旁邊寫作,即時給他協助和建議,這樣既有「出門去工作」的感覺,又有「有人陪我做事」的感覺。在我的經驗裡,這兩種感覺都更能讓人想要行動。
另一個打算,是我把另一個也想寫作的大孩子找來禮拜三一起聚會。我盤算著這兩個寫作的孩子聚在一起的話,也許可以有一些良性的競爭和合作,最好也可以有一些討論。
無法行動的身體:我們為什麼逃避
沒想到聚會的時間到了,我幫他揪的寫作伙伴也到了,這孩子遲遲卻沒出現。我打給他媽,才知道他這兩天狀況不好,整個人陷入無法行動的厭世狀態。我請他聽電話。
我:你要來嗎?
孩:我……。
我:現在來還好啊,還有兩個小時可以做事欸。
孩:(沉默)。
我:好啦快出門。
孩:……那我還要四十分鐘左右喔。
掛上電話,我其實就知道他不會出現。果然,他媽傳訊給我,說他對於自己忘記聚會感到很內疚也很焦慮,但他不想出門。我回訊息跟他媽說:「沒關係,你就支持他的決定,我再看看怎麼辦。」
最後這孩子傳了一個訊息給我:「我今天還是不過去了」。那個「還是」,在我看起來,有一種艱難。
在我的經驗裡,有種類型的人會時常遇到這種艱難,但我一直搞不清楚究竟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態。直到讀到Iris M. Young的「陰性身體」和「陰性猶豫」概念時,我才稍稍有了點頭緒。
Young說:「在實踐軀體任務時,女人的身體雖然確實帶領她朝向其意向的目標,卻往往是以迂迴繞行而非自在直接的方式,在嘗試與一再定向的努力中虛耗許多動作,而其原因往往在於陰性猶豫。」
Young引用傅科的觀點,指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時刻被觀看、安排、引誘或推動,使得女性安排身體的能力被抑制。但人對自主的期望沒辦法被完全壓制,這使得女性既有一種「我能」的計畫,一邊又有「我不能」的自我否定。
我在之前的文章裡把這個概念挪用到現代小孩身上。在現代的教養觀和現代學校體系裡,小孩(無論性別)的身體跟過往的女性身體一般,長時間被觀看、評價、安排(利誘或推動)。這可能就是許多成人(無論性別)都擁有「陰性身體」的緣故。
過去在面對這種「陰性身體」時,我常常一籌莫展,能做到最好的情況,大概只有不批評他們的行動,以免增加他們的罪惡感,避免他們進一步自我否定。
但這一次跟這位孩子的合作經驗不太一樣,我們有了一些進展。
「假裝做了決定」,用逃避來逃避逃避
這些年我跟很多陰性身體的人合作,累積了不少經驗跟觀察。
我們的教育環境最早的根源,是來自對壓制、威權和一致性的反叛,於是顯得極端自由自主。在我們同事教育者之間通常沒有上下關係,這使得教育者得要在許多層面上下決定,像是要上什麼課、要怎麼上、為什麼這樣上、怎麼收費、什麼時候開始招生、要收多少人,在許多的教育現場都是被規定好的項目,在我們這裡全都要自己決定。
有些時候,我們的同事會陷入一種「沒辦法決定」或「雖然決定了但沒辦法行動」的狀況。當我跟這位孩子的媽媽交換充分的資訊後,我覺得這位孩子的身體,可能也在陰性猶豫的狀況裡。
為了確認這一點,我在隔天下午殺去他家,到他們門口對著裡面大喊:「欸欸阿溪,我們去吃飯!」他聽到我的聲音,從房間裡走出來,戲劇化地躺在地上大喊:「啊啊你怎麼來了!啊啊你真的來了!啊啊啊啊!」

編輯配圖
我小心翼翼推進,試探他的狀態:「走啦一起去吃飯啊,我好餓。」
他在地上耍賴了一兩分鐘,終於站了起來,走進房間穿外套、拿錢、開門出來,我們一起走出去吃飯,一路上慢慢聊天,他的表情也從一開始的陰鬱漸漸變得開朗。
在小吃店的餐桌上,我提出我的建議:「我們來做事吧!做事就可以一掃陰霾!就像你現在跟我出門,你心情就變好了。」
他覺得有道理,於是我們吃完後買了瓶奶茶回他家,各自打開電腦開始工作。他決定要把他這兩天的狀況寫出來,於是我們一邊藉由討論釐清他的狀態,一邊試著斟字酌句地寫下來。
我們討論的重點,圍繞著為什麼他會決定不去參加禮拜三下午的聚會。在對話中,他不斷使用「逃避」、「罪惡感」、「很廢」、「沒力氣做事」這幾個說法,引起我的注意。我試著核對這些想法的來源,發現他其實很重視禮拜三下午的聚會,也很想要出席,但就是下了一個「我今天不去」的決定。
「你一直使用逃避這個字,所以你是真的決定了你不去嗎?」我靈光一閃,把「逃避」跟「決定不去」兩個狀態放在一起,向他確認。
他仔細想想,發現他其實並沒有決定不去,那種狀態比較像是在逃避。他接著描述自己逃避之後的狀態:「我後來就跑去打電動,一邊打電動一邊又沒辦法開心起來,一邊打一邊有罪惡感。我覺得我在逃避我決定不去這件事。」
所以他做了一個「假的決定」(這是他的用詞),但那其實是在逃避,並不是真的決定,他只是順著當下的情況(待在家裡)而已。然後他為了逃避這個「假的決定」帶來的自責(很廢、沒有行動)、內疚(爽約),躲進電動裡,用他的詞來說,他「用逃避(躲進電動裡)來逃避逃避(下了假的決定)」。
他恍然大悟地說:「難怪我在這種情況下打電動的時候都不開心,越打越不開心,但越不開心就越想打,什麼事都不能做。」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當天我們為了這種情況設定了行動方針,我們說好,假若他往後遇到這樣的情況,要盡早讓我知道,我們要盡快採取緊急行動計畫,像那天那樣,盡快投入某種有生產的行動裡,不要沉溺在逃避的惡性循環裡。
「可是你為什麼要逃避?」我當天沒有問他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太難,我還是自己先想想比較好。
「為什麼要逃避」的問題,其實在我們這一行並不很陌生。長久以來,自主一直跟逃避纏繞在一起,我們大多時候都不是跟有主動性的人在一起工作。
在這兩週裡,我一直斷斷續續在思考這個問題,直到我在一本新書的未定稿裡看到Erikcson的發展階段論(雖然只是在參考資料裡的一句話),但線索連接了起來,我覺得我好像搞懂了什麼。
下決定的心理能量與發展階段
Erickson提出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論有八個階段,每個階段有主要的任務。他也主張,如果上一個階段的任務沒有獲得充分的發展,則會影響下一個任務的發展,甚至導致下一個階段發展的失敗。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這種把人生進程標準化的理論,但發展階段論在這時給我一個啟示:如果做選擇有難易之分,並且個人面對不同難易程度的選擇,會耗費不同的能量,那麼我們就可以解釋陰性身體的狀況了。(這跟發展階段論有點像,但其實不太一樣。我不認為這些事情有前後順序之分,而只有難易之別)
假若陰性身體的來源是過去那些總是被安排的日子,那他們應該會十分缺乏下決定的經驗,也同樣缺乏依據決定採取行動的經驗,這使得每一次下決定跟每一次根據決定而採取的行動,都非常耗費精力。
比方說,一個從小被管理者安排要不要刷牙、要不要吃糖、要不要睡覺或起床、要不要學習的孩子,一旦離開管控的時候,他要面對各種大大小小的決定──不,我們應該說,他要面對各種很大很大、超大超大的決定──如果連要不要睡覺、要不要刷牙都要花費心神去考慮,那要不要打那個人、要不要跟這個女孩交往、要不要換工作這種程度的決定,所需要耗費的心理能量必然十分巨大。

不能決定要吃什麼、吃多少、要不要吃完,是許多孩子的日常
於是我們會發現,這樣的人一旦進入缺乏強勢指導的框架中生活時,他會在各種決定中很快就耗盡心理能量。這種推論可以解釋前面那位孩子的逃避狀況、在罪惡感與自責的無間地獄裡輪迴。
我還想到一種孩子,那種日常生活裡極有壓力,來到我們這裡就完全不管不顧,只能隨著當下的直覺行動的孩子。我過去總以為這些孩子不負責任或無能負責,從沒想過他們可能是在之前的決定裡用盡了能量。
也就是說,這些人不是不下決定、逃避或不負責任,而是沒有能量下決定了,只能任憑直覺帶領他行動,做出看似下了決定的行動或回應。
有些人比較需要規則,嗎?
「不是逃避,而是沒能量作決定」這個推想讓我想起一位同事,他在我們的現場裡有時會顯得進退失據,並且也飽受罪惡感、自責和自我否定的折磨。然而當他離開教育現場,進入一個十分規律的職場後,他發現他很有生產力,不但能夠完成工作上的要求,甚至還能在職場進行非典型的教育工作和人類學觀察。
我曾經非常困惑這位同事的經驗,一度想要接受,人其實就是分成兩種,一類是適合在框架中生產的人,一類則否。但還好我沒有輕易接受這種想法,於是我有了新的觀點。
也許跟過去那種幾乎沒有框架的職場相比,這位同事現在的職場確實是比較適合他的,但卻不是因為他是一個「適合在有框架的職場工作的人」(這種觀點總是太輕易把人分類),而只是因為他的陰性身體還不習慣做那麼多的決定。
於是這個推論也能解釋,為什麼有些孩子被強力規定的時候可以有很好的「表現」,但在沒有強力規定的時空裡,卻像一攤爛泥或總是做出相反的事情。這並不見得是因為那個小孩需要被規定,反而可能是因為過多的規定讓他錯過下決定的經驗,而在日後無法面對複雜的、需要頻繁下決定的世界。

連午飯吃什麼都是我們每天要面對的問題,現實裡很少能有「我全都要」這種單純明快的決定……
從小開始鍛鍊「決定力」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個老詞後面加個力好像就變成全新的東西。反正就是從小讓孩子下決定,小孩就越來越會下決定。
一方面是因為,有許多時常遇到的選擇對小孩來說將會駕輕就熟毫不費力,甚至就變成一種他自己建構的日常習慣。以我家小孩來說,他在下午之後大致上不會去吃巧克力,這是他在二到六歲之間千錘百煉之後的「最終看法」。當然,代價是他無數次吃完巧克力之後像是發酒瘋那樣傻笑鬼叫,然後睡不著哭著指天咒地怨天尤人,以及我們兩夫妻無法睡覺而上升的肝指數。
去上課這件事情,對我們家小孩來說也是幾乎不用決定的事,偶而他心情不好,或有什麼原因而不想去,也是說不去就不去,不會猶豫太久。
另一方面,考慮到長大後所面臨的選擇,通常比小時候所要面對的選擇更複雜,而且後果也更嚴重,所需要耗費的能量應該也會越高。一個從小沒什麼鍛鍊決定力的孩子,一下子要面對各種複雜困難的決定,八點起床十點就把能量用完,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最後不免俗來吹噓一下決定力的重要。大家都知道世界的變化越來越快,一成不變的工作越來越少,有越來越多的工作不再有SOP,而需要從業者快速下決定並且採取行動,決定力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了(是說我也說了四千字)。大家一起來鍛鍊決定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