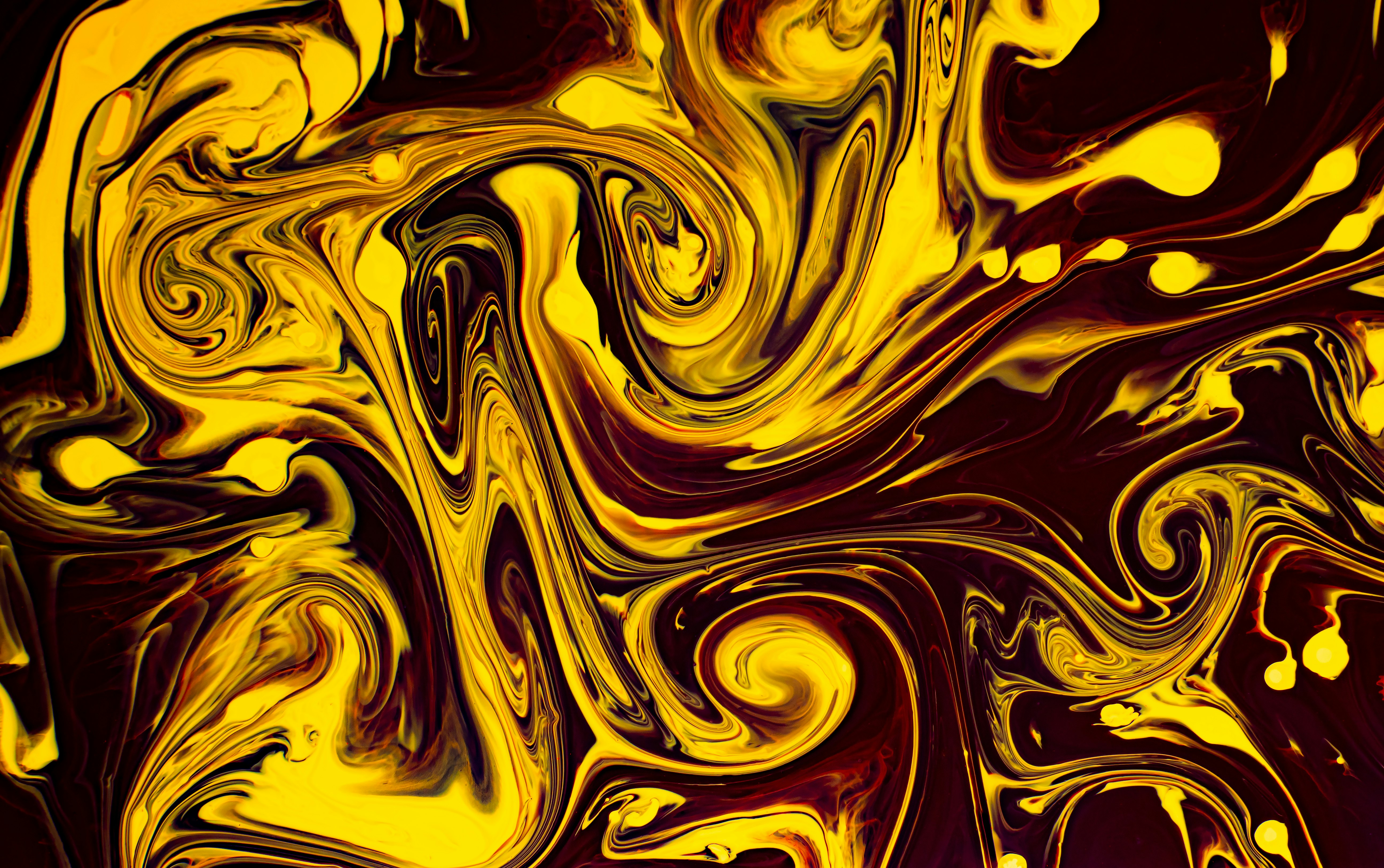作者:精神科專科醫師 簡婉曦
發表日期:2022/10/24
本文彙整自精神科門診的診間絮語、認知行為治療與正念認知心理治療的經驗,所有對話皆已改寫,去除所有可以標示出特定身分的描寫。若有巧合,請勿對號入座。
「憂鬱症」三個字看似簡單,卻是許多人的心魔。罹患憂鬱症就像罹患癌症一樣,好像是某種絕望的象徵。為了替代「憂鬱症」,許多人選擇引用其他名詞來代稱自己的「憂鬱症」。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整理了一些常見的替代名詞。
憂鬱症的替代醫療名詞之前在《【憂鬱腦學】憂鬱症的汙名化》文章中,我們曾經介紹過憂鬱症常見的污名化現象。然而,阻礙憂鬱症治療的魔王裡,除了外界或個人自我的汙名化現象,有些人運用替代醫療名詞來阻礙憂鬱症治療的發生。這樣的替代行為,一部分原因來自於外部汙名化作用,另一部分,可能是來於一個人心理拒絕承認憂鬱症的存在、挫折感與反抗。
被憂鬱症患者或其身邊的人選擇,用來取代憂鬱症的醫療名詞有很多。臨床上,最常聽到的有:抗壓能力不足、失眠或睡眠不足、自律神經失調。
抗壓能力不足
在臺灣,排名第一的憂鬱症替代性醫療名詞是「抗壓能力不足」。
抗壓能力不足,源自於人與人比較出來的評分標準,也和原生家庭的成長環境、家庭價值系統與自我評價有關。
相比起憂鬱症的治療模式,抗壓能力不足更像一個賺錢的商業模式,也是一個值得託付與持續努力的目標。由抗壓能力不足衍生出來的抗壓性增長訓練課程或書籍,廣受許多憂鬱症患者與其家屬接受。許多患者也很習慣將自身的憂鬱症歸咎於自身的抗壓能力不足。
然而,事情真的是如此嗎?如果在您心中有過這樣念頭閃過,不妨想像一下,您自己想像的抗壓能力充足,究竟是建築在甚麼樣的假設基礎與證據上。
在所有憂鬱症的族群中,青少年與成年初期的憂鬱症患者最容易被怪罪抗壓能力差。然而,抗壓能力本身就是一個假議題,就像拿張飛比岳飛,很多時候無法直接相比。
大部分診間裡的個案,是過度努力、企圖達成自己或家屬遠大期待的「人」。不少人努力到比八點檔連續劇還要精采,卻還是要面對旁邊支持系統的責備與自身的道德批判。許多人生故事裡的努力甚至光怪陸離到到不病才不正常。
真正與憂鬱症有關的特質,其實真的不是抗壓能力;真正與憂鬱症有關的特質,其實是過度努力與社會推崇下產生的旺盛企圖心。
與青少年和成年初期的憂鬱症患者相反,對老年憂鬱症患者來說,抗壓性比較少被拿來作為責備的理由。畢竟要子代或晚輩去責備長輩抗壓性不足,臺灣人相對不習慣,文化上也傾向攻擊子代或晚輩不懂得同理老人家。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不但建構出抗壓能力本身定義的荒謬性,更顯示出,抗壓能力只是一種社會定義的價值,與憂鬱症無關。
失眠或睡眠不足
失眠或睡眠不足,是另一種常見的憂鬱歸因。
在臺灣,一直有一種文化在鼓動,過度強調「睡得好,治百病」。
的確,睡眠在精神科與其他醫學領域扮演重大角色。病患每次返診精神科門診時,我相信許多醫師也會反覆詢問患者的睡眠狀態與睡眠品質。然而,除了刻意熬夜、輪班、賀爾蒙變動、老年睡眠時相前移等外在或內在因子,睡眠常常是評估一個人精神狀態,包含憂鬱或焦慮症狀的結果,而非是疾病的原因。
如何改善睡眠品質很重要,但只治療失眠,就像發燒只吃退燒藥。發燒的人,可能得到的是感冒,可能是COVID-19病毒,也可能是癌症。
臨床上,在老年憂鬱症初診患者的用藥紀錄中,常見到患者長期服用高劑量的安眠藥或後線安眠藥,有些憂鬱症患者的憂鬱病程其實已長達20年以上,卻只是長期服用安眠藥。在青少年或一般成年人憂鬱症初診族群中,濫用安眠藥物的比率較低,使用藥物病程也較短。
在正常治療劑量下,服用安眠藥對於憂鬱情緒沒有任何改善效果。如果服用安眠藥可以改善情緒,可能改善的是睡眠焦慮,而睡眠焦慮,常常與患者的安眠藥物成癮有關。
憂鬱症患者,在臺灣,鎮定劑與安眠藥成癮的比率相當高。有一部分特定憂鬱症患者,可能會濫用臺灣人最喜愛的某種特定安眠藥,因為在過量使用下,患者不但睡不著,還會陷入某種記憶模糊、片段、似夢似幻的放鬆或愉悅狀態。這樣的濫用是危險的。
換一個角度來說,一個人對睡眠的期待,有時候剛好呼應一個人憂鬱症的嚴重程度。
在嚴重憂鬱症的患者中,有一群人會呈現睡眠過量的情形,他們一天會花上10到15小時以上的時間躺床休息與睡眠。由於躺床時間過長,食物攝取量減少,腸胃蠕動不佳,營養失衡,肌肉萎縮,身體不適增加,長時間睡眠下,即便清醒時也仍自覺疲倦。對這些患者來說,他們常會想再「多睡」一點,自己將睡眠藥物服用到2倍到3倍以上劑量,卻發現不管自己睡多久都睡不飽,身體健康還越來越差。
事實上,在憂鬱症治療時,反而是要減少鎮定劑、安眠藥物劑量,重視生活結構調整、照光治療,且要限制躺床與睡眠時間長度。憂鬱症治療時,晚上睡眠固然重要,但白天規律起床活動更重要。
(接續下一篇《【憂鬱腦學】憂鬱症的替代醫療名詞(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