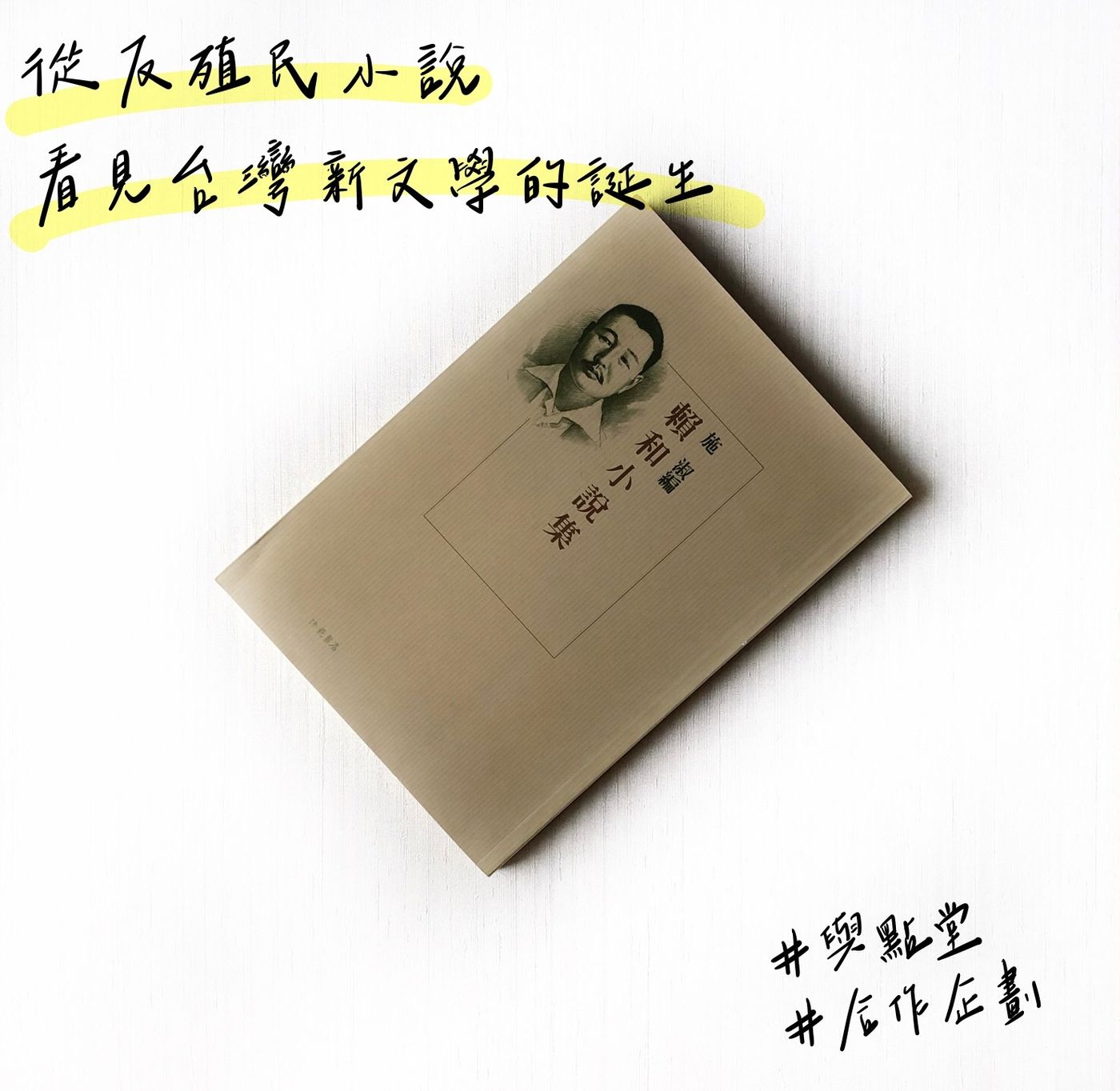【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臺語是粗俗、沒有文化、無法用來講述高深學問的語言嗎?如果有人這麼講,就拿《內外科看護學》打他的臉(最好不要,這本書很珍貴)。距今已經超過一百年前的1917年,英國人戴仁壽醫師編寫了這本書,全書分40章、657頁、503張圖,內容包括解剖、生理、護理等學問,最驚人的是——整本書是用臺語寫的。
如果可以用臺語來書寫醫學,那麼當時以臺語使用人口比例為大宗的社會,應該會跟著出版不少這樣的書吧?可惜事與願違,這種用臺語書寫的教材,並未成為醫學用書主流。究~~竟,是文字侷限了發展?還是政策成為了阻力?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內外科看護學》能夠成為國立臺灣文學館的典藏品,無論怎麼看,都是異數中的異數。
因為這是一本教人如何看護病人的醫學教科書。

就算請到什麼大文豪來執筆,無論詞藻運用得如何典雅趣致,灌腸依然是灌腸,燒燙傷仍舊是燒燙傷,不會成為足以放進國文課本或世紀散文選的文章。
那為什麼《內外科看護學》擁有此等殊榮?是因為它出版於1917年,已經一百歲了,所以我們應該敬老?還是因為作者戴仁壽是一名為臺灣奉獻了歲月的外國醫師,讀他的行述不掉眼淚簡直不是人,所以我們應該尊賢?都不是,這本教科書能夠成為臺灣文學館重要藏品,原因只有一項:它是用白話字寫的。
白話字,又稱教會羅馬字,由19世紀外國傳教士引入臺灣。外國傳教士為了能快速學會臺語,決定暫且將數量龐大的漢字先放一邊,單純把臺語當成是像是英文一樣,只要用拼音就能寫出來的語言;另一方面,為了讓臺灣諸多未受教育的文盲,能夠快速讀寫識字,也傳授給教徒這套拼音符號——不,在他們的信念中,這並非如同今日「ㄅㄆㄇ」一樣只是拼音「符號」而已,而是與「ABC」一樣的拼音「文字」。於是一句簡單的問候「你好」,教徒不需要認識「你」「好」兩字,也不必記得這兩個字的部首、結構、筆劃,單純拼音出來寫成「lí-hó」就行了。這是真正實踐了「我手寫我口」的大白話文字,因此又稱為「白話字」。
早期的白話字文獻,大多是傳教之用,文字也淺白。《內外科看護學》則樹立了一個典範:臺語文原來也可以用來闡明專業學科、精深知識。這本書,的的確確是臺語文的一塊榮耀里程碑。
當時全臺使用臺語者,佔了大多數;現代醫學又是當時新興學科,人人趨之若鶩,有《內外科看護學》成功開了先例,這種用白話字書寫的教科書,應該從此大為風行,倣效者眾吧?可惜事情的發展常常出人意料,這樣的書籍縱然並非絕響,也一直是冷門中的冷門。

以此書為例,用白話字寫的醫學教科書,預設的讀者是誰?序文開頭便點明:一是病人,二是臺灣人或使用廈門腔的人,三是外國傳教士。然而這本書的真實讀者,不太可能是一般病人或一般醫療人員,這可以從政策與文字兩種侷限來談。
西式醫療在臺灣發展的歷史,除了西洋傳教士自清末便開始引進之外,1899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也正式成立授課;校規第一條開宗明義說明主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為授予本島人醫學教育,養成醫師之處。」在注重培育優良醫師的政策下,這種民間的醫療看護修習,自然逐漸被淘汰。當病人在醫院裡忍著疼痛,看著醫護人員在自己底下又挖又擦又灌又抽,開口閒聊「先生你真厲害,應該是醫學校出來的乎?」心裡期待的答案當然是YES,不會是「我其實是閹豬的,工夫攏靠這本《內外科看護學》學的」。
除了政策越來越時不我與,本書用白話字書寫,事實上也設下了相當大的限制。當時的文盲雖多,但社會畢竟是根深蒂固的漢字場域。日常生活隨隨便便就會來個轉角遇到字:考試、對聯、經文、碑文、看板、匾額、佈告、傳單,老百姓買來念著消遣的「歌仔冊」,全部都是漢字。事實上,就算白話字能讓一個文盲在短短幾個月內能讀書寫信,但他身旁親友也得是白話字使用者才行,否則也是無用武之地。所以在彼時,白話字使用者幾乎都是教會內信徒。
戴仁壽在編寫此書時,事實上也遇到相似的問題,使他無法完全拋棄漢字。在序文裡也特別提出這件事:許多專有名詞,在臺語白話中尚未存在,必須從其他「漢字文化圈」如中國、日本借來。例如「腦腫瘍」、「三尖瓣」,許多術語都必須在白話字之後括號標注漢字寫法。從這本書裡,可以觀察到白話字使用者,運用臺語的文音系統,可以引進外地的漢字詞彙,直接融為臺語的一部分,並借助漢字工具使論述更明確。
可惜,時過境遷,在可預知臺語即將滅亡的眼前,這本書更顯得孤寂。縱使精通臺語醫學詞彙,今天在醫學院也用不著了,徒然成為身擁「屠龍之技」卻無龍可屠的窘境。這是臺語的哀愁,也是這本書如今反而顯得珍貴之處。

★ 作家小傳
戴仁壽(1883-1954),英文名George Gushue-Taylor,加拿大紐芬蘭島人(出生時屬英國,後被劃分為加拿大)。醫師兼傳教士。1911年與新婚夫人來臺行醫,並學習臺語,此後斷斷續續奔走英國與臺灣兩地,至1954年過世時,在臺時間二十餘年。1917年出版《內外科看護學》,以及將最新的醫學技術引進臺灣,尤其致力於痲瘋病的醫療,是他最偉大的貢獻。戴仁壽夫婦安葬於今樂山療養院紀念園中。
★延伸閱讀
★ 觀測員簡介
黃震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文系碩士,藏書人、說書人、拿著藏書說書之人。與黃哲永合編教材《讀冊識臺灣》、與吳福助教授合編《臺灣傳統漢語文學書目新編》,著有論文《取書包上學校:臺灣傳統啟蒙教材》、散文《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散文《藏書之家:我與我爸,有時還有我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