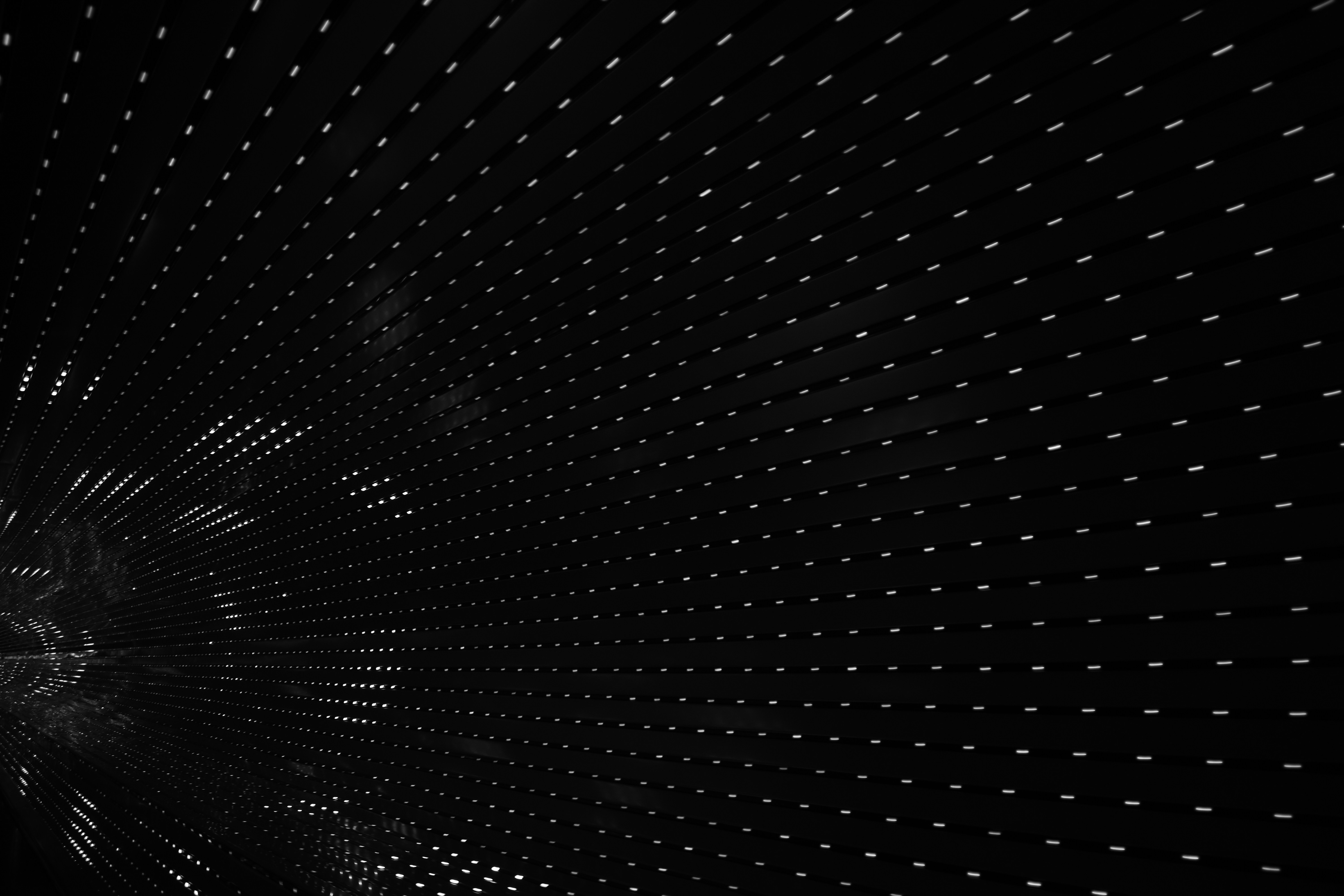方格精選
我可以是一個化胎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今天跟一群高中生們開同學會。我和這群少年從他們三四年級時開始每週定期聚會上課,直到六年級。後來他們各奔東西,長出各自的身高和智慧。
其中有一個少年問我:「現在上課的小孩裡,有跟我們當初一樣的人嗎?」
於是我們開始聊起過去的他們,有的是怎麼整人,有的是怎麼好笑,有的是怎麼勇敢。還有的,是怎麼樣關上心門。
「有小孩跟我一樣有『被罵模式』嗎?」
「有啊!那時候我跟你講話,還要一直搖你說『欸!醒一醒,我是盧駿逸啊!你把我當成誰了?我沒有要罵你!』」
「有有!我還記得,哈哈哈。」
在長大的過程中,有些孩子會因為某些原因,決定要關上門,躲進內心世界裡。我的工作之一,是去敲這些孩子的門,一而再、再而三,像是把「鍥而不捨」刻在額頭上那般,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在這樣的情境裡,我有時覺得自己彷彿看到敏感易碎的心靈悄悄地將心門打開一絲隙縫,打探外面的狀況。當他看見我仍等在那裡,有時我像是聽見鬆一口氣的嘆息,「啊,你真的還在那裡」,像是這樣的感情,從門後面傳來。
通常我就是等在那裡,偶而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或者刻意發出一些聲音,讓門裡的孩子知道「我還在這裡」。
心門裡的混沌
那一天,有個我在門外等了好一陣子的孩子說,他要來我的營隊擔任助教。這個營隊其實不缺人力了,除了我之外,我已經有一個全職的教育者、一個來幫忙的大人、三個大小孩。除此之外,我知道這個孩子還沒有完全走出來、還在「對世界時不時有敵意」的狀況裡,不但可能幫不上什麼忙,反倒會佔去我的時間跟力氣。
我在考慮要不要答應的時候,想到哈雷彗星。我想著他好不容易要試著從門裡走出來了,我真的要錯過嗎?這種機會就像彗星一樣,要是錯過了這一次,下一次會是什麼時候呢?
我答應了。然後開始心裡準備。
那一天,他來了,一開始仍然是笑的。但快節奏的工作氣氛對他來說是全新的環境,加上他是中途加入,很多情況搞不清楚。我試著交派工作給他,他做了一些,拒絕一些。
一件一件工作持續地進行著,看著我不斷交派工作給其他孩子,他跑來問我「我要做什麼?」我說了一個工作,他拒絕。我又說了一個工作,他還是拒絕。
我知道他還在「想要幫忙」跟「不想要被命令」中間迷失方向,於是不打算太勉強他。我說:「那你就看自己想做什麼吧。」
但他光是待在那裡,壓力就不斷重疊累積上來。其他大孩子助教(看起來)都知道自己在幹嘛,他卻不太知道。報名參加營隊的小孩子們都有自己的東西,他卻沒有。
累積太久的能量終於爆發,他喊著「你對我不公平」,牽了腳踏車就要走。我擋住他,不讓他離開。我們開始爭執,爭辯助教的工作範圍、爭辯公平。他詞窮了,轉而哭著嘶喊「你就是覺得我很爛,我爛我走可以吧」。
我沒有退讓,我從頭開始,一次次算出我對他的支持與接納,也一次次算出我長久以來看見的、他的才能、智慧與寬容。
但我知道這一切討論都不是真的,他只是在面對這個殘酷的、不如己意的世界時,耗盡了當下所有的力量,又沒有能夠坦然無畏地尋求支持的依靠,而想要躲回內在世界裡去。
他想要證明他果然不值得被愛,而我果然不會如我承諾地那般愛他。
他放下腳踏車,往另一個方向跑。我跟著他過去,隔著兩三步的距離。他一直走,我就跟著。他說「你不要跟著我」,我說「不要」。
等待生機
我在心裡想像,把「鍥而不捨」刻在額頭上。
我們在鄉間小路裡繞著,一圈一圈,大概到了第三圈,他走到堤防邊,靠著堤防,蜷縮在一起,像是回到那個全然被接納的子宮裡。
還好,有個同事來探班,我知道那裡有值得信任的年輕教育者,還有我陪著長大的大孩子們。於是我讓自己安心地待在這裡。
我坐在堤防邊,看著對岸的樹,陽光,風。我已經很久不帶錶了,我也不打算拿出手機。我要忘記時間,子宮裡面沒有時間。我也要忘記營隊,子宮裡面沒有營隊。
孩子坐了起來,拿出背包裡的麵包,開始吃。像是艱難地再生出來一次之後,身體感到飢餓。
「欸,你竟然有吃的。」我笑著說。他沒有回應。
吃完後,他回到了營隊裡,慢慢跟其他人互動,慢慢笑了出來。
吃著點心,氣氛好的時候,他又笑著來問我:「我要做什麼?」
我說:「你去陪那幾個小孩做蔥抓餅?」
「我不要。」他笑著說。
「……等一下蔥抓餅做完你幫忙擦桌子?」
「我不要。」他笑著說。
「……等一下擦完桌子你幫忙把桌子復原?」
「我不要。」他笑著說。
「……你說說看助教是要幹嘛的?」
「陪小孩做事、幫忙收拾東西。」他笑著說。
「……好喔。」
客家人有一種以子宮為比喻的風水造景,叫做化胎,通常在建築物前後,可以集天地之靈氣,育化建築物裡的人或靈。
我生來沒有子宮,但我想我可以是一個化胎。
為什麼會看到廣告
660會員
121內容數
我和朋友共同分享、推動「合作式教育」的概念,試著建立由父母、小孩與教育者共同合作、建構的教育場域。在這個寫作計畫中,我想要寫下我在教育現場的記錄及相關問題的思考,希望能讓讀者和我一樣,在繁雜的教育/教養現場得到些微的救贖,且保有討論和省思的空間。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