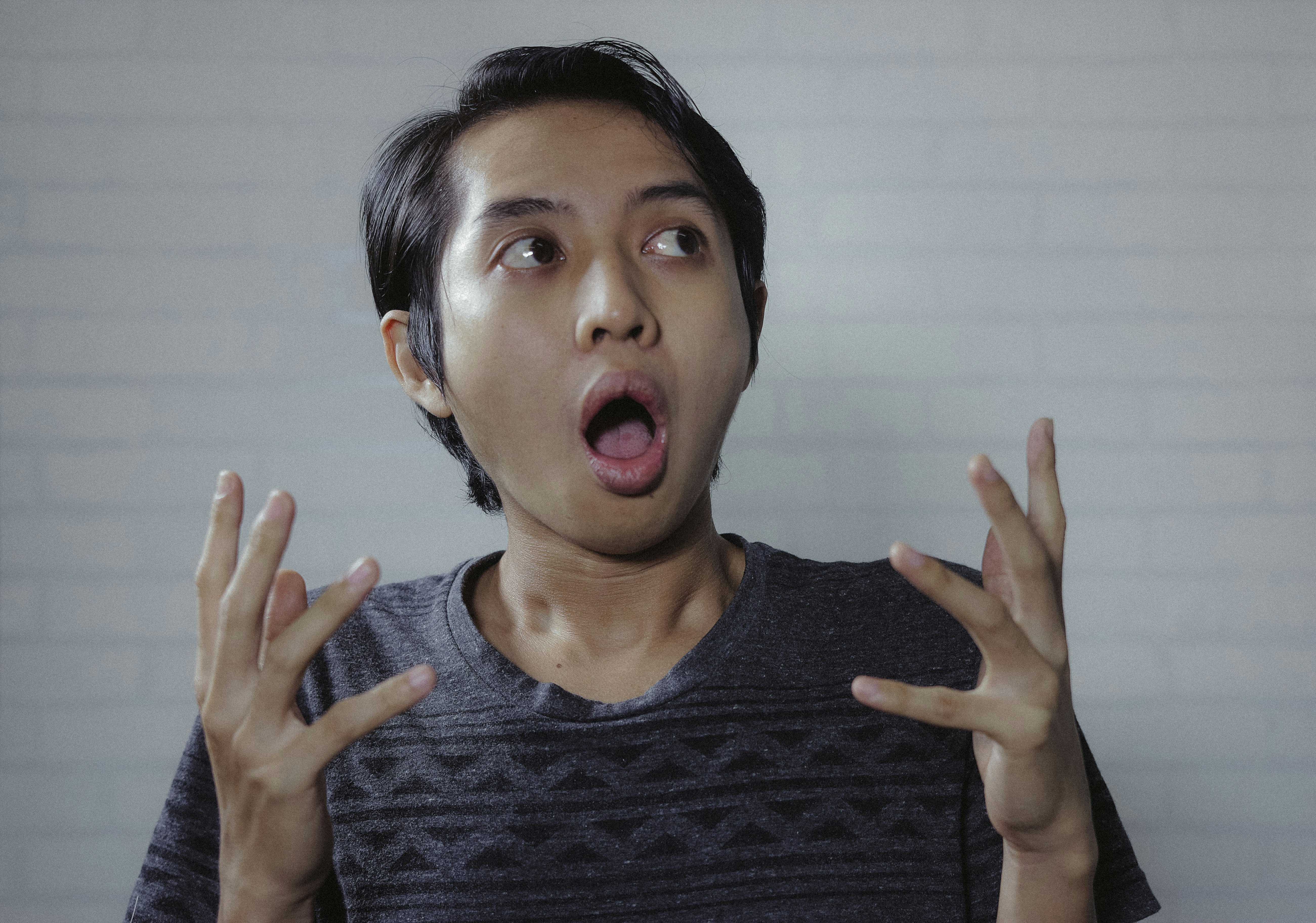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裡,被輿論稱為「吹哨者」之一的醫師李文亮,於2月6日過世。關於李文亮僅僅是在非公開通訊群組裡,向親友告知他看過「類SARS」的診斷書,就被有關當局以「造謠」為由處分的相關的過程,在網路上可以Google到許多訊息,這裡就不贅述了。他也曾在微博上轉貼支持香港警察的貼文,可以想見在這個事件前他很可能不是所謂「異議人士」。
而這篇文章要討論的,著重在中共有關當局當初要求李文亮簽寫的「訓誡書」。

「公安機關希望你積極配合工作,聽從民警的規勸,至此中止違法行為。你能做到嗎?」
「我們希望你冷靜下來好好反思,並鄭重告誡你:如果你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你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你聽明白了嗎?」
在這份李文亮於1月3日簽署的訓誡書裡,這兩個問題在格式上分別都留下了「答」的欄位,在這兩個欄位上,李文亮分別寫下「能」以及「明白」。
後來李文亮自己及家人都被感染。1月31號,李文亮在病床上透過社交媒體上寫下被當局傳喚的始末。2月6日晚間,李文亮死於新型肺炎。
當初簽下訓誡書的李文亮,心裡想的是什麼呢?在病床上的李文亮,心裡想的是什麼呢?
雖然是那個國家的事情,但看在我這個教育者的眼裡,卻像是近在咫尺的事。相同型式的文件,通常被叫做「悔過書」,有時會要當事人自己寫,有時叫你悔過的人,會指示你如何寫。像是這樣的東西,有許多人都有寫過吧?
即使沒有寫過,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問句?
「知道錯了嗎?」
「知不知道你錯在哪?」
「下次還要不要這樣做?」
面對這些問題?你懂不懂得怎麼回答?
「懂。」
你一定跟李文亮一樣,知道該怎麼回答,才能「脫身」。
教育現場的三個故事
(1)
有一次,在課堂上有一個創作的練習。下課的時候,我跟助教阿虎看孩子的作品。阿虎指著一位孩子C的作品對我說:「他都亂貼!」我心想:「如果隨便貼,拿回家媽媽看到,說不定就會誤會孩子沒學到東西。」
我隨口問了:「其他人呢?」
阿虎說:「都貼對了。」
我說:「那要確定他認真貼,不能太隨便。否則回頭要跟媽媽解釋,挺麻煩的。」
在那之後不久,就有了下面這段對話。
孩C:「你不是說可以亂貼嗎?」
我:「那是另一個,不是這個。」
孩C:「我貼好了啊!」
我:「你是照抄別人的,不是自己貼的。」
孩C:「我有認真貼!」
我:「我現在很認真問你,請你也認真回答。你有認真貼嗎?我很認真上課,所以我希望你也認真貼,如果你說謊,那你就是在欺負我,這是你要的嗎?」
孩C:「我……我沒有認真貼。」
在兩天之後的早晨,助教阿虎和我分別埋首撰寫觀察記錄,阿虎突然問我:「那天你有說要孩子『貼正確』嗎?」
正分神在寫作的我毫不猶豫、直指本心地回答:「沒有吧,懂就好了,幹嘛一定要貼正確。」回答完過了一會兒,這句話的意義才慢慢在我腦中顯明。

我停下工作大叫:「啊!難怪他那時候說『你自己說可以亂貼的啊!』」
(2)
我家外面就是一間安親班。有一次我跟孩子經過門口,有兩位老師堵在門口聊天。用「堵」這個字,就真的是那個意思。教室的門沒有比一般家戶的門更大多少,兩位老師分隔兩側靠著門邊在說話,中間的剩下一個小小通道。
有幾個孩子總裡面追逐出來,我跟我家孩子剛好走過。其中一位A老師突然出聲叫回最後的那位孩子:「OOO,過來!」
被點名的孩子乖巧地走到老師面前。
A老師說:「你剛才撞到B老師了。」
小孩看著A,什麼話都沒說。
A老師接著說:「B老師很痛。」
B老師配合著摸自己的手臂,表演疼痛的樣子。
小孩看著A跟B,還是什麼話都沒說。
A老師又說:「你要跟B老師說什麼?」
小孩立刻懂了,他說:「對不起。」
A老師滿意地說:「好,你可以走了。」

小孩回到他的玩伴裡,兩位老師回到原先的話題裡,像是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如果我們對成年人這樣做,可能會被解釋成沒事找事,或是在耍流氓)
(3)
我剛入教育現場的頭兩年左右,曾經去一所小學代課。早自習的時候,有個秀氣的小女孩走上講台,開始記名字。
我好奇問他:「你在幹什麼?」
女孩說:「我在管秩序。」
我初來乍到,一切都還搞不清楚狀況,就由著她管秩序了。大概二十分鐘過去,女孩在黑板上寫下了許多數字。
然後就是上午的課程。經過幾節課之後,小孩跟我比較熟了,有幾個下課時間開始跑來找我聊天。
他們問我:「什麼時候要處罰?」
「什麼處罰?」
「就記座號的啊。」他們指著黑板上的數字。
「為什麼要處罰?」
他們支支吾吾地說不上來,最後跟我說:「因為之前都有處罰。」
「我不處罰人。」我鄭重地說。
到了中午,那女孩又走上講台。孩子們開始監視彼此,互相告狀。這個孩子說那個孩子其實眼睛有張開,那個孩子說這個孩子偷偷笑。我宣布:「不要裝睡了啦,你們不一定要睡覺,不過醒著的人要安靜,不要吵睡覺的人。」
話一講完,大半的孩子都抬起來頭看著我,過了幾秒,他們就笑嘻嘻地開始做自己的事。有的看書,有的畫圖,有的跟其他人眉來眼去比手劃腳。
我轉頭看女孩,女孩有點不知所措。我問她:「妳想睡覺或做自己的事嗎?」她點點頭。我說:「妳去吧。」
女孩走下講台,趴在桌上,沒多久就睡著了。
下午的下課時間,跑來閒聊的小孩變得更多。負責管秩序的女孩也來了。
女孩說:「老師你真好,都不會處罰人。」
「對啊,我不會處罰人。」我一邊看他們的作業,一邊回答。
「可是,這樣也有不好。」另一個女孩說。
「有什麼不好?」我抬頭看她。
「這樣我們就不會乖。」
「你是說,我不處罰你,你就不會乖嗎?」她有點猶豫地點頭。
「我不相信。」我說。
隔天中午午休時,負責管秩序的女孩來問我:「我要記名字嗎?」我笑著說:「妳想記就記吧。」女孩笑瞇瞇地跑去睡覺了。

我們教育現場裡的形式與管理
在(1)的例子裡,教育者以為自己有一個教育上的理由,但從小孩的角度看來,卻很清楚是莫名其妙的、形式上的要求,而小孩在極大的權力差距的威逼之下,不得不服從於教育者指示,做出屈辱的退讓(按:另一方並沒有做出任何讓步,至少就辭典上的意義這絕不叫「妥協」)。
在(2)的例子裡,小孩十分習慣於這種服從與退讓,並且養成了敷衍的、配合形式的、揣摩上意的行動方式。
而在(3)的例子裡,小孩甚至以這種形式來捏塑自己,將自己理解成「不處罰就不會乖」的樣子,來合理化自已無力抵抗的現實狀況。
我想藉由以上三個故事,指出一個遍行於台灣教育現場的共同點:
教育者的權力極大,小孩習慣於服從這種權力差距,而這個社會也很習慣於小孩對教育者的無條件服從。
在這樣的教育現場裡,大人們看不見小孩的處境、看不見小孩對情境的理解、也看不見小孩的慾望、需求與意見。
當然,在我們的教育現場裡,大多數成員都是日復一日地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教育者和小孩不過是順著文化上日復一日累積而成的習慣,而做出各自的行動。然而,李文亮所面對的,也是本質上同樣的情境,公安和李文亮也是順著過去日復一日的習慣,分別做出訓誡和認錯的行動。
也是因此,這樣漠不經心的、注重形式與管理的教育現場,直直指向的就是李文亮簽名的那紙訓誡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