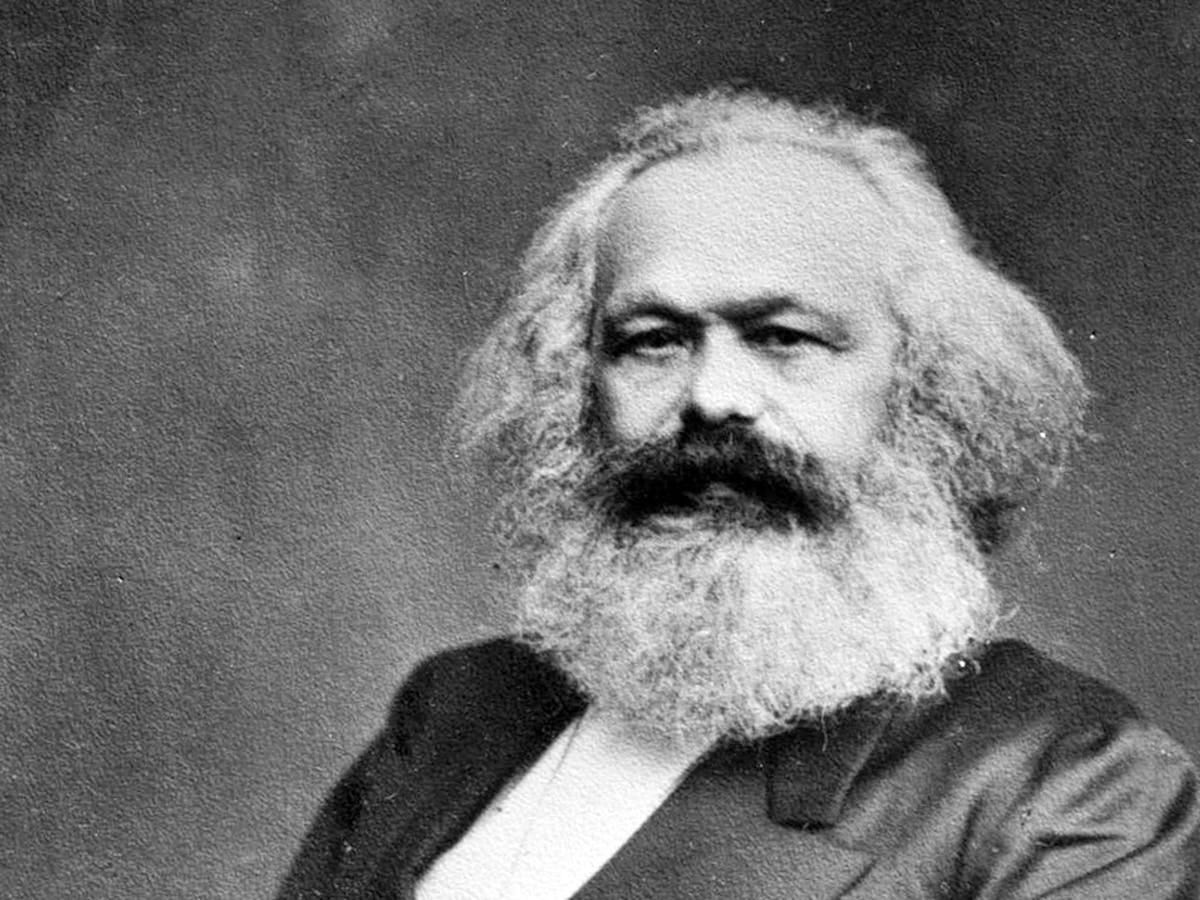(一) 〈大媽媽的葬禮〉
《馬奎斯小說傑作集》志文版的譯者楊耐冬,對於〈大媽媽的葬禮〉是這樣子敘述的,他說:「〈大媽媽的葬禮〉是寫極權者的龐大勢力下,那些醜陋的事情是怎樣地在排演。大媽媽就是那個惡勢力的頭頭,她象徵極權者的權威,她那個共和國的總統、民間領袖、財閥,以及教皇都要向她俯首,聽命於她。馬奎斯認為她是一切人民災禍的來源,所以用死亡來結束她。」
如果楊耐冬的「極權者」是指「個別的獨裁者」或是「資本主義」,那我覺得他錯了!因為馬奎斯在小說中安排的兩個橋段──大媽媽死前向公證人說出的那一長串看不見的財富清單,以及她對該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控制手段──很明顯指向哥倫比亞的天主教教會,以及那些不論族裔而支持教會的有權有勢者,我認為,這些可統稱為天主教勢力。
「……大媽媽費了很大的力氣抬起半邊屁股──這個姿態也是她的祖先在死前表示權威的一種方式──以跋扈而虔誠的聲音,卻記憶模糊地對公證人說出那一系列看不見的財富。
計有地下財富(指未發掘的礦產)、水域資源(指未捕獲的魚類等水產物)、彩旗(指榮譽的標幟)、國家權力、舊有黨團、人權與民權、統御權、申訴權、國會聽證權、推薦函、歷史紀錄、自由選舉、美麗皇后們(指皇族特權的一種)、卓越的演說、大示威遊行、出類拔萃的年輕婦女、有才幹的紳士、呆板的軍人、超越的陛下、高等法院、不准進口的進口貨、自由放任的婦女、肉類管制、語言的統一、以身作則、受約束的新聞自由與出版自由、南美的雅典精神、輿論、民主的教訓、基督的道德觀、外匯的短缺、貧民的權利、共產黨的威脅、國營船運、高昂的生活費用、共和國的傳統、受特權壓迫的階級、政治擁護的文件等。」(上、下文的部分,詳見志文2004年重排版第217、218頁。)
「那天晚上和接著以後的幾個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可視為往後歷史的教訓。不僅是因為基督精神──這種足以激發最高權力的個人崇拜,也是因為否定個人興趣與判斷能力的不同,以至對一個突出的個體安葬變成人民自慰的共同目標。許多年了,大媽媽靠了她那三箱偽造的選舉證件,使她得到了一部分私人財產,因此她在自己的帝國裡保有了社會和平與政治和諧。為她服務的男人──她的屬下和佃農,不分老少,一個世紀來不僅運作了他們自己的民權,也玩弄了已死的選民的民權。在政治權力轉變的過渡時期,她也先行利用了傳統權力。對普通人民,她先行控制了階級,假借遺傳的智慧優越感壓制民意。在平時,教會聖職都由她控制,當然聖職的薪俸以及與她有關的人事也是由她控制,她甚至操縱秘密活動或選舉以達目的。在混亂時期,大媽媽暗中給她的黨羽提供武器,且公開支援她這邊的受難者。她這種愛國狂熱就是她自由最高榮譽的保證。」(上、下文的部分,詳見志文2004年重排版第220頁。)
除了大媽媽的家世、財產、性格、言行,馬奎斯也不餘遺力敘述教皇、大主教伊撒貝爾、共和國總統接獲大媽媽死訊的反應,更不吝惜筆墨描寫大媽媽臨死時所接受的繁冗宗教儀式及遺產處置,這並非偶然,馬奎斯就是要透過這些敘述、描寫向我們展現:能輕易得到外援的哥倫比亞天主教教會、哥倫比亞民族主義(愛國精神)、造就貧富懸殊景象的政經體制,如何相互為用,讓眾多哥倫比亞人無法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也讓哥倫比亞的政治人物、各領域的知識人不願或不敢針對全國或是所在的工作崗位提出改革方案。總之,就我的閱讀經驗來看,馬奎斯筆下的「大媽媽」應該是指「以梵帝岡為首,對哥倫比亞各方面具有強大深遠影響力的天主教勢力」。
(二)〈人造玫瑰〉
《馬奎斯小說傑作集》志文版的譯者楊耐冬,對於〈人造玫瑰的人造人造人繼〉是這樣子介紹的,他說:「〈人造玫瑰的〉是寫一個女孩不願將失戀的隱私給人知道。乍看之下,沒有什麼,其實,馬奎斯是探討一個嚴肅的問題:隱私權。在政治獨裁的社會裡,人民的隱私權常被剝奪,秘密警察無需法院的搜捕令或拘票,就可以抄家捕人,還有暗中電話監聽等,無不是嚴重地損害了人權。」
但說實話,這篇小說我實在讀不出馬奎斯有這樣的涵意。那位揭穿女孩謊言並發現失戀秘密的瞎眼女人,是女孩的祖母,而對方發現以後,並沒有對女孩施暴或者辱罵,反而還因眼盲、情書成功被女孩銷毀,無法理直氣壯向女孩的母親告發。如果說馬奎斯想隱寓什麼,我倒覺得是揭露哥倫比亞當時的社會風氣非常保守壓抑,少男少女自由戀愛原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小說主角卻得要極力隱藏一切。

(三)〈星期六後的一天〉
楊耐冬在〈馬奎斯的生平和《馬奎斯小說傑作集》〉一文,對於〈星期六後的一天的人造人造人繼〉是這樣子介紹的,他說:「〈星期六後的一天的〉寫一個象徵心靈腐壞的大祭司是怎麼地被人藐視而讓人走避。……馬奎斯藉著這個故事諷刺某些宗教團體與教會人士,諷刺他們不做真正心靈的解救工作,而製造聖靈與惡魔的荒誕故事,結果愚弄別人不成,自己卻成了被唾棄的對象。」
確實,我讀到的是一個年老、頭腦昏聵的神父,無法用當時的科學知識解釋麻鷸大量死亡的現象,也無心深究鳥兒暴斃的原因,只是一昧襲用古代教士的作法──以惡魔與上帝對抗這種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勉強解釋,結果無法讓莉貝卡、市長及其他市民安心,反而使他們對神父的知識、精神狀態心生疑慮,而不願參加神父主持的彌撒。神父的悲劇在於,他不了解自己的聽眾老早就不是百年前、幾十年前的哥倫比亞人,古代行之有效的作法,現在完全無效。抱殘守缺,不思改變的下場就是信徒紛紛遠離,甚至改投他教或成為無神論者。
只是「神父愚弄他人」的說法,我持保留態度,畢竟馬奎斯筆下的神父並非蓄意編造謊言騙人,實在是這個角色的思想非常固陋保守,跟不上時代,用中世紀那套世界觀過日子。馬奎斯有意以這個角色隱喻當時的哥倫比亞天主教教會,極端落後保守,與現實脫節,不僅無法讓人們鼓起勇氣,面對災難或未來,反而引發人們的恐懼,讓人們除了信上帝、祈禱、做彌撒,就不知所措。至於楊耐冬說,馬奎斯在這篇小說試圖「探討熱情與理性的和諧」(楊耐冬/語),我實在讀不出有什麼地方在探討「熱情與理性的和諧」問題。
(四)〈巴扎沙驚奇的午後〉
楊耐冬在〈馬奎斯的生平和《馬奎斯小說傑作集》〉一文,對於〈巴扎沙驚奇的午後的人造人造人繼〉是這樣子介紹的,他說:「〈巴扎沙驚奇的午後的〉寫有錢人的吝嗇,沒有錢的人反而慷慨,結果是吝嗇擊敗了慷慨。吝嗇永遠在那歷史的軌道上過著敗德的生活,而慷慨卻永遠是個以酒澆愁的窮人。這個故事的生活悲劇感,使人讀後產生一種『罪惡是富人的特權』的感覺。」
我讀了以後,沒有那種『罪惡是富人的特權』的感覺,而且也不覺得馬奎斯在傳達這個意念。當然,馬奎斯是藉著「巴扎沙不顧孟提爾的反對,堅持將籠子送給孟提爾的兒子」,以及在彈子房(撞球場)的誇張言行,嘲諷、挖苦孟提爾那種貪吝、為富不仁的有錢人,在第161頁,他寫道:
「『我們必須做許多東西,在富人們死之前賣給他們。』他說,他已爛醉如泥。『富人們都病倒了,他們都快要死了。他們是那麼樣地小氣,以致連生氣也不捨得生出來。』他兩個小時來一直在付點唱機點唱的錢,因為他一直在點唱,沒有中斷。人人都為巴扎沙的健康、好運、財氣,以及富人的死亡而乾杯,他們同時也各自離開了彈子房,把他獨個兒留在那裡。」
馬奎斯設計出來的這個橋段,實在很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