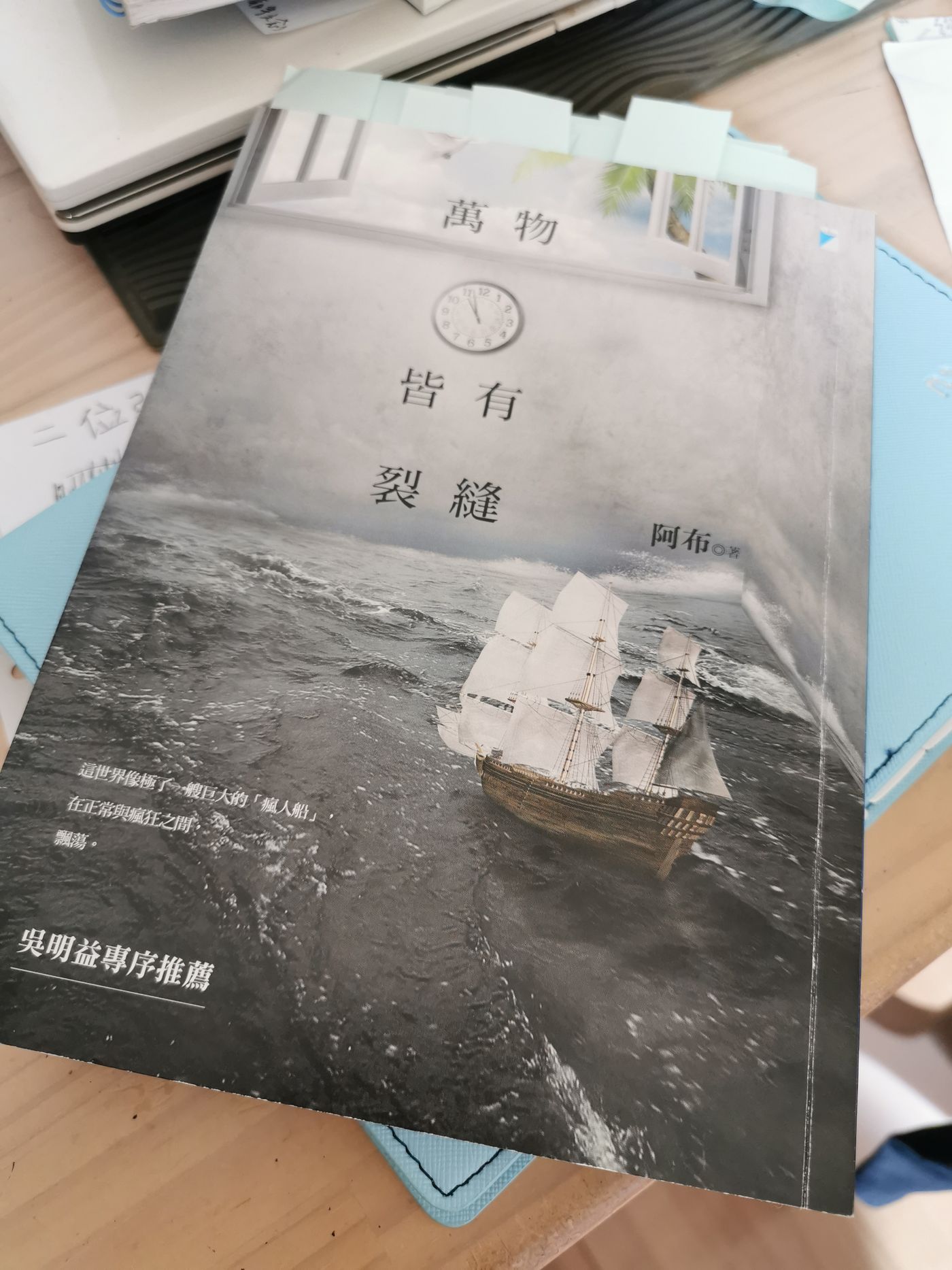性愛與戀愛之間的曖昧:讀許俐葳《我有一個關於不倫的,小問題》
曖昧之所以讓人受盡委屈,是因為找不到相愛的證據;而牽扯上不倫的曖昧,一旦開始了擁抱的勇氣,就會讓人變得貪心。與其說是「不倫」,這本小說更像是在描繪「戀愛」,只發生在小房間的戀愛,沒有房卡所以被困在電梯的戀愛,沒有共同日常生活的戀愛,關於只能被化約為三小時、關在小房間裡的戀愛的各種「小問題」。
我們之間到底是性愛,還是戀愛?這是在不倫關係中,最曖昧也最讓當事者拼了命地想找出證據的小問題。

許俐葳《我有一個關於不倫的,小問題》
從身體開始的關係
不倫故事的開端有許多種版本,有些從欺騙開場,有些從坦白開場,也有些從隱瞞開場。雙方不論在初始或過程所期待的關係,有些是性愛,有些是戀愛。當雙方進入一段不倫關係,有些是從身體開始,有些是從情感開始,也有些是在兩端游移擺盪的曖昧。許俐葳的《我有一個關於不倫的,小問題》,小說中的兩組不倫關係,都是從身體開始陷入的。
有次,小捲用非常非常害怕,簡直餘悸猶存的語氣告訴我,「身體好可怕。」我想她要說的是,身體好誠實。(P. 15)
有人堅持性愛合一,有人相信性愛可以分離。有人說,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動物,只要不反感,就可以發生性行為;而女人是感情的動物,必須要是喜歡的對象才能上床。有人說,男人其實很重視感覺,他們沒辦法和不喜歡的人接吻、撫摸、做愛。那女人呢?我好像沒有印象看到特別針對女人無愛而性的論述。(如果有,請分享給我,感謝。)
能否將性與愛分開,與性別無關。在討論性愛是否合一時,其實我們更像是在探究不討厭、喜歡、愛等肉體之外的情感面,究竟是壁壘分明,或者是一道光譜,抑或是一個發展前進的軌跡?
我想要被摸。我想要好好地被摸。像這樣的要求,可以視作一種求愛嗎?——那樣的愛,究竟是什麼呢?它有名字嗎?它能夠被指認嗎?它能夠度過世間一切難關嗎?它讓我的身體發出從未有過的水聲,到底是因為查理,因為愛,還是因為這一切未曾體驗過?(P. 36)
小說中以第一人稱敘事,女主角「我」與男主角查理的偷情,其實一開始是查理說要談戀愛,但「我」知道查理是已婚者,因此否認了彼此「談戀愛」的可能性。直到倆人的身體碰觸在一起,對於彼此身體的吸引與渴望,是無法假裝的真實反應。但是,這種吸引與渴望,究竟是純粹的生理反應,或者同時揉和了另一層的情感需求呢?在正視雙方對於彼此身體的渴求後,「我」開始想知道是否有身體以外的答案。
被戀愛打亂的關係
不倫故事的情節,如果只有性,似乎就不精彩了。那樣的故事也許會像八點檔本土劇一樣,演員可以一直參與演出,直到被導演或編劇賜死為止,或者演員自行辭演。所謂的不倫之所以精彩,通常是倆人的關係曝了光,或者任何一方對於這段關係,有了超乎性愛的期待。儘管是對方先開始的,是對方先開口說想要聊天的,是對方主動提出要談戀愛的,然而一旦另一方開始想從這段關係中,尋找倆人不僅止於性愛的戀愛證據時,這段關係就變得脆弱不堪。因為是不倫,所以其實倆人的關係在離開只能做愛的小房間之後,就什麼都不是。
不是什麼?不是可以隨便打一通電話叫對方幫忙的關係,不是能自在大方介紹給工作夥伴的關係,不是可以安心逗留在房間的關係。站在不斷下降的電梯裡,我感到口腔乾乾的,還沒有刷牙呢。在那睡意完全被剝奪,強烈驚慌失措,其實僅是幾十秒的空白裡,我腦子裡充滿了巨大的恨意,為這個所謂的「不是」。這難道不是一件小事嗎?(P. 129)
第三者被排除在法律、道德規範、社群網絡之外,成為一個不合法的存在,因為不合法,所以沒有任何權益保障,儘管只是打電話求救這樣一件日常小事,也沒有權利。
小說中的「我」,或許並不在於證明查理與她之間的關係是性愛或戀愛,也並不需要取得存在的合法性,而是透過找尋戀愛證據的過程中,想確認自己是被愛的,不僅止於身體,還包括情感面。
孤單的不倫關係
當小說中的「我」陷入對於查理的愛,她開始從倆人相處的細節中,想瞭解查理與他太太的日常生活與相處互動,甚至想認識查理的太太是怎樣的一個女人。而愈是探究,愈明白自己始終只是第三者,是這段不倫關係中,感到孤單的一方。因為查理與他太太之間,儘管也許不做愛,但他們離不開彼此,他們會聊天,他們是家人。
我的電梯理論,或許在我和查理身上並不適用。那部電梯裡關著的,始終只有我而已。(P. 139)
儘管如此,小說中的「我」對於查理的太太,比起嫉妒,我想更接近的語詞是愛慕。或許愛慕這個詞有點滿,但「我」與其說是想取代查理的太太,倒不如說是想成為像她那樣的女人。或許就像是謝曉陽的詩集《不要在我月經來時逼迫我》裡所說的那樣,因為喜歡對方,所以喜歡對方喜歡的人、味道、物。
我喜歡他
我喜歡他身上的味道
我也喜歡他的太太
我喜歡她身上的味道
他們用同一塊肥皂
我喜歡那塊肥皂的味道
我喜歡那塊肥皂(《不要在我月經來時逼迫我》,P. 50)

謝曉陽《不要在我月經來時逼迫我》
閱讀書目
許俐葳(2023)。《我有一個關於不倫的,小問題》,遠流。
延伸閱讀推薦
謝曉陽(2021)。《不要在我月經來時逼迫我》,印刻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