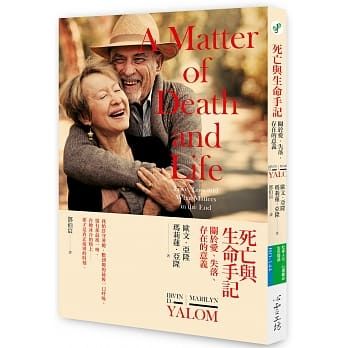致謝 Savoir 刊登本文:https://www.savoirtw.org/article/4523
說到桑塔格很難沒有人聽過,就像對文青提到村上春樹一般,這也是書名以「桑塔格」為名的緣由,即便在書裡頭作者 David Rieff 都以「蘇珊」稱呼他的母親。原先認為這會是種消費,畢竟所有人都認識桑塔格,但沒有人認識桑塔格的家人,即便如作者作為子嗣且為作家,但他無論在外國或台灣的境況幾乎都是較為罕知,我也不例外。然而,在閱讀過程中卻漸使我改觀,這並不是一本打著我母親是桑塔格的暢銷書,而是對於一位知識份子從旁側寫的報導紀實性文學,且也正正因為作者具有血親的身分才能讓我們看見這些。
但這樣的紀實著作,是否道德?這有些像是卡夫卡的書籍被違背其意願而出版一般,但若布洛德沒做這樣敗德的事情,20世紀文學不會有那麼大的動盪。不過在桑塔格這裡的情況有些不同,因為《泅》一書並非其自身的著作,而是旁觀者的見證而為之紀錄。雖然殘忍,但也揭露了一些關於死亡的樣貌。桑塔格(Susan Sontag)死於 AML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但在這之前已經經歷過與癌症的「戰鬥」,在上個世紀癌症就如同當代的黑死病一般,能存活下來更是個奇蹟,在近代的個人主義之後,「…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卻是人之為人的一項特質。」(頁143),桑塔格也不例外。甚至在經歷這種統計上的異數經驗後,更會對此產生更大的嚮往。只不過,任何的存活都只是種延命,「…能夠做到至少把許多癌症轉變成『慢性』疾病而非不治之症那麼,我們就只好死於其他疾病了—對付這些疾病,我們沒什麼更好的辦法,而且它們也拖不了多長時間。」(頁153)
獲取越多的知識將會使人墮入更深的死亡幽谷,就像桑塔格無神論一般無法將宗教當作鴉片一般吸食,沒有任何安慰,沒有彼岸作為精神的寄託。死了就是死了,即便再怎麼把自己當作特例看待,然而,「如果正如我相信的那樣,我母親一直以來都想像自己與眾不同,那麼,他最後一次的疾病殘酷地揭示出這種自負的脆弱性。這體現在它無情地讓她遭受痛苦和恐懼。」(頁150)所謂的公平(Fairness)一直都是規範意義上的,因為事實上的公平不存在,除了死亡。
惟,死亡是唯一的事實上公平,因為沒有例外。
有戚戚之感正是我總把「知識是我唯一的信仰」當作信條,但經由作者對桑塔格作為知識份子的死亡見證,正好會讓對於知識信仰者感到驚恐。桑塔格在面臨厄疾時汲汲於獲取更多的知識,但獲取得越多越是揭露現實。求知是種對真相的渴求,但難以想像的是真相對自己是殘酷時,我們該如何「接受」—而接受是與知道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我母親活多久都不可能活夠。她醉心於活著;就這麼這麼直截了當。」(頁132)熱愛生命者否認死亡,即便我們都能認知到的死亡並非對立於活著的對立概念,而是在生命循環中的一個環節—最後的環節。
在上個世紀資訊尚未如此發達時,作者提到醫病關係中經常出現的是對於病人的欺瞞,這種白色謊言固然出於善意,但也是權威的知識壟斷,同時,也是家父長主義的表現。但會否揭露現實是即便對於如同桑塔格般的人格也是無法承受之重?「…殘酷的現實面前,假使醫生沒有把病人當贏而的本事—意味著消除恐懼,讓患者心裡踏實,而非居高臨下,或者在她面前逞什麼威風—我母親在死之前幾個月就已經瘋掉了。」(頁127)即便作出無數的哲學分析包括說謊的不道德、家父長行為的自主性剝奪,但在真切面臨到這種道德決疑時是否我們仍能如此抽離地審驗命題?
桑塔格無法想像沒有她的世界如何存在著,其實,我們都無法想像沒有自己的世界如何存在著。我們無法去設想我們未觀察到的事物就「在」那兒,我們是在我們思考的情況下證驗自身的存在,這是笛卡兒式的思想基礎,問題在於,我們無法思考時,存在又是怎麼一回事?外於我的世界在「我」已不思考,不存在時,又是如何存在?
我們無法思考無法被我們思考之事物。
活著就是走在步向死亡的林蔭路途上,從來沒有康莊大道,也沒有英靈殿等著任何人前往,那些都是活著的人編織出的神話,包括宗教亦同。若不是有這些神話,誰能願意忍受此世的苦難—被獅子啃咬、在戰場給長矛刺穿?
「…然而,當然,想要與死亡達成最低程度的妥協,其實就是活在當下。如果你看戲看到第三場卻還在期待接下來的兩場,那麼,曲終人散的前景是令人難以忍受的。…」(頁32)「活在當下」似乎已是浮濫正向思考的箴言,但活在當下卻是我們所不得不,除了時間是我們所建構出的概念而已之外,對於未來的盼望其實都是虛妄,因為真正的未來對我身而為人的我等而言,只有死亡:純粹的滅。
作者所測寫出桑塔格的經歷中,讓我想到我們每個人都將跟阿茲海默症患者一般無助,腦部越是發達者對於患病而言是墜落地越快,同樣的,桑塔格對於知識的渴求越是強烈,讓她越是難以面對作為人將必然面臨的終局。「然而,她死去了,她經歷的是其他癌症患者也會經歷的死亡,她肯定漸漸地相信這一點—在這樣的死亡中,知識沒有用,抗爭的意志沒有用,醫生的醫術也沒有用。...」(頁143)不過縱然如此,在這種種的虛無中,對於存在的意欲卻是最為強烈,「她認為世界是個藏骸所...但她怎麼活也活不夠。她認為自己不幸福...但她即使不幸福,還是希望能活多長,就活多長。」(頁135-136)
桑塔格的死亡歷程(這裡所指的是從確診到死亡之間,而不包括整個生命)是緩慢而痛苦的,因為她想活著,無法接受死亡的同時也去嘗試所有一切能繼續活著的可能—即便人的最後可能只有死亡一途。只要在最後是能讓生者能趕到些許安慰,即便這仍然是令人感到懼怕的描述,
「她的死是安詳的,就像死亡一樣;我是說,她死時幾乎沒有痛苦,幾乎看不見任何的焦慮。她就這樣走了。她先是深深地吸了口氣;停了四十秒(如果你看著一個人死去,這四十秒是一段令人極其痛苦、不知什麼時候會戛然而止的時間)。然後又深深地吸了囗氣。這樣只持續了幾分鐘。然後停止就成了永恆,這個人已不再存在,斯蒂芬·尼默說:『她走了。』」(頁152)
所有生者無論作為、不作為都將帶著罪疚感繼續活著,因為無論做了什麼、沒做了什麼,對於以「生」相對於「死」的二元觀念中,任何作為對於死都無法否定,卻只能延緩。死亡之海並非臨終者所獨游於其中,而是在看著、寫著、想著、活著—或說,存在著的人們,的存在實際境況。
「…當她去世時,我們在她的死亡之海中,陪著她一起由著,看著她死亡。然後她真的死了。至於我自己,我發現我仍然在同一片死海中泅泳。」(頁149)

picture credit:https://www.savoirtw.org/article/4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