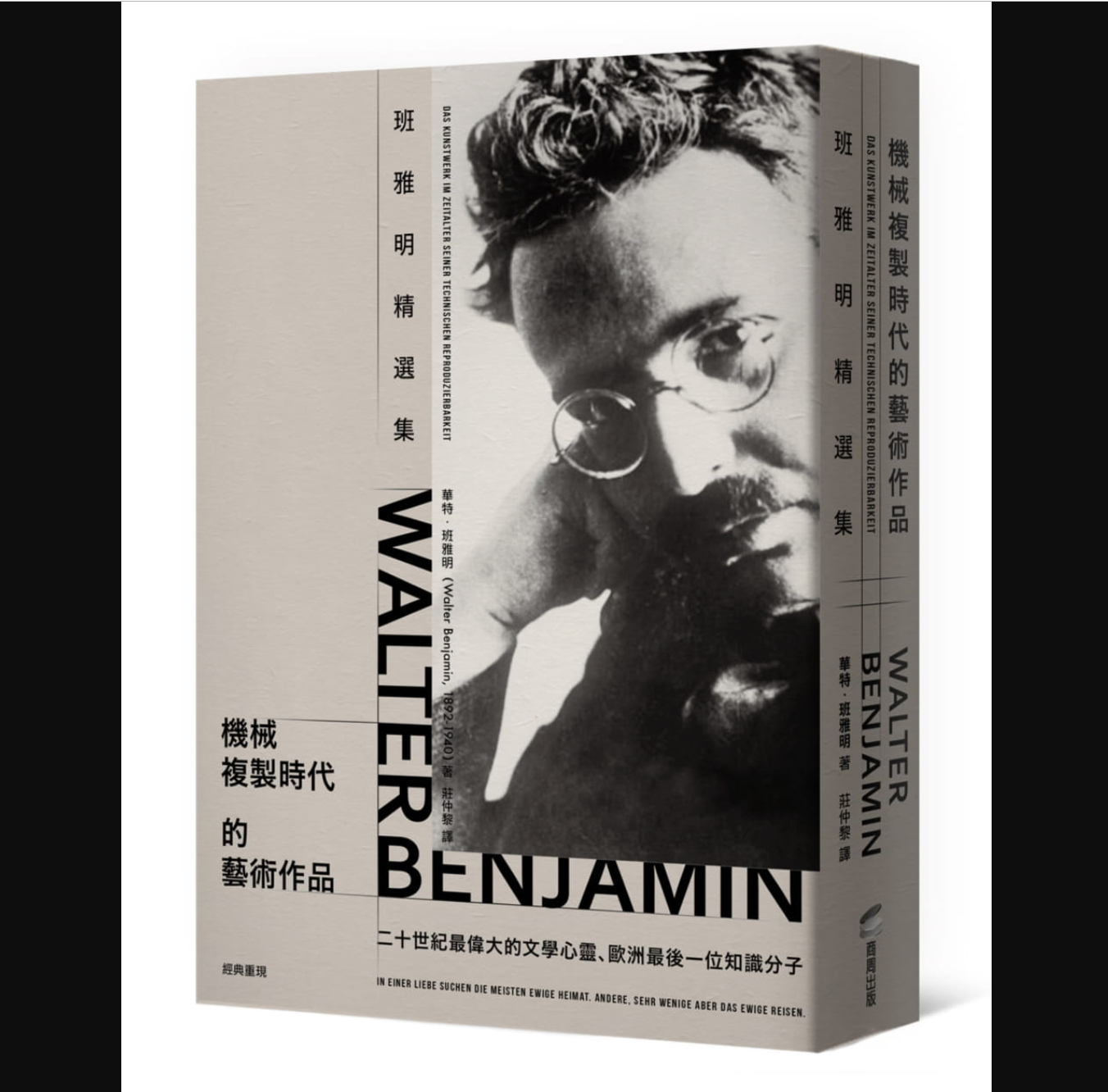〈《記憶與救贖》讀書會(六):歷史書寫的「星陣」與「引文」〉2024-08-17
關於歷史書寫,班雅明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比喻意象,這個意象也見諸於其認識論立場之中。也就是星陣(或另一些翻譯所謂的「星叢」)的結構。透過星陣,班雅明試圖回應一種自古希臘就存在的哲學問題--「理念與(物質)現象」之間的關係。
對班雅明來說,理念並不能直接被理解為一種高於(超越於)現象的概念或法則,也不僅僅是某種抽象,而更像是一種我們把握到現象的方式。一方面來說,我們需要透過星陣或星座來辨識出那些被凸顯出來的星星的位置;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那些星星,星陣根本無法存在。
當人們將天幕中的星星「瓜分到」星座之中認識的時候,物質層面與現象層面上的星子並未被否決,相反地,它們被以星座的方式充分利用。
歷史也是如此。人們誤以為存在有某種理想的「客觀歷史」,相信歷史是按照時間序來排列,甚至在此基礎上賦予一種進步論的解釋。然而,即便是最自認中立的史學視角,它終究是將(無論文字或非文字的)史料篩選並排列在一段「尚未被書寫過的歷史脈絡」當中,任何人無可避免地是用「某種星陣」去把握它們。
既然所有歷史在第一手的時候就都已經是抽離脈絡並被重新賦予新脈絡的了。我們就有必要進行歷史批判,去揭露出當前被普遍接受的那種「客觀的」、基於時間序的歷史書寫同樣只屬於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星陣。並必須要給出那個能夠將被壓抑的星子解放出來、重新認識的另一種歷史書寫。
*
當然,這種被要求的「新的」歷史視角並不是任意的,而是奠基於當下此刻與「已逝的過去」間的辯證關係。在這個新的歷史書寫中,過去的歷史被以「引文」的方式和當前的敘述並列,如同在星陣中的星子,與這些時間序上不連接的時刻共同被閱讀。
在這裡,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兩者之間的關係既不是過去單方面地將此刻照耀,也非此刻單方面地將過去啟明。而是如同押韻一般,兩者呼應地被同時把握。根據Sieburth的理解,引文和此刻的評論或思想應該被視為相同的位階。或者,我們也可以將之想像成,除了過去被引用,此刻也以相同的強度被引用。並且,這一史學的引述,也能夠在接下來的時刻一再地繼續被引述。
在布朗肖(Blanchot)的解讀中,藉由「最後的日子」之歧異性,「末日」與「最近的日子」重疊在了一起。於是乎,末日審判就不能被抽離地理解為將全部被保留到遙遠「時間的終點」才發生,而是每一個日子、每一個「正義的行動」發生的日子,都該被視為審判發生的「最後的日子」。
這種思路也呼應了過去提到過的:我們每個人都分享了「一點點微弱的彌賽亞力量」。我們每一次對歷史的進一步引述,都能被理解為法庭上的證言,讓我們對世界歷史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更貼近正義真相的裁決。
唯有這樣如「持續翻譯」般不斷地引述,才能將歷史客體盡可能朝向其「應該成為的樣子」被呈顯出來。一直以來被錯過的正義、解放、與所謂的「救贖」,才有機會在歷史批判裡面發生。
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