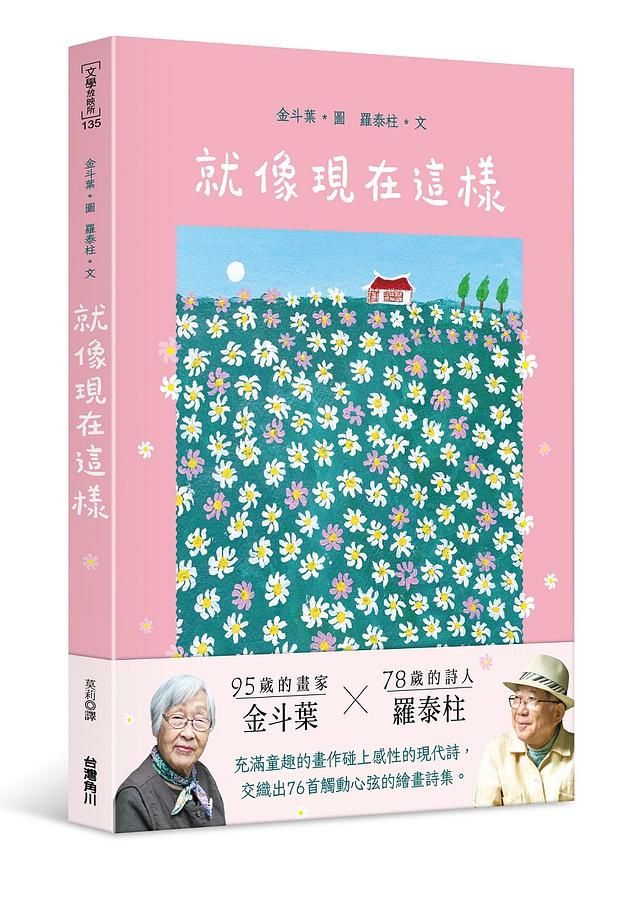在這樣普天同慶的日子裡,你會想起那個她嗎?
我記得的她,總是溫順地應和著他的每個強硬的指令和三不五時從口中飆出的國罵。
我記得的她,身為家中最小的女兒,卻不小心嫁給家中食指浩繁的長子,從婚後第一天起,就註定了她燃燒自己的青春和氣力,給那一大家子,也給自己再生家庭的一家子。
因為躲避空襲,她只上了幾年的小學校,但直到60、70多歲,她仍記得那些五十音,仍記得那些她少數可以運筆寫出的字。
如果身分證上的生日是真的話,她可能是克勤克儉的金牛座,但也有可能是性格剛烈的牡羊座,但無論如何,她沒看過自己的命盤也沒算過自己的流年,她只接受任何命運給予她的功課,無論那在外人看來是多麽痛苦的考驗,畢竟活著本身,本就該是每天的奮鬥。
下田、碾米、洗衣,只要能讓貧困的家裡多點餘裕的活她都做,而且要做到讓人無法挑惕,因為她最怕的或許就是大家庭裡那些妯娌的耳語,還有那些說好聽是雞犬相聞,說難聽點是左鄰右舍八卦的眼光。
她的生命裡,總是有那些隱形的他人在看著她的一舉一動,那些隱形的人總會用教條式的規訓框著她,雖然她的世界裡只有先生和孩子,但她總覺得隱形人會不斷地鞭策她,成為一個更好、更賢慧、更體貼,永遠是比較級的人種。
61歲時丈夫因為車禍意外過世,她的天就此崩塌,從此耳邊不會再有聲如洪鐘的國罵,也不會再有讓她夜不成眠震耳欲聾的鼾聲,她也彷彿失去她視為宇宙與生命運作規則的引力。在那之後,她試著學習成為自己,那個雖然冠夫姓卻沒了丈夫的未亡人,那個在丈夫還在時,從沒有自己意見的自己。
再次進到國小補校,雖然只上了快兩年,但她工整有力的字體,常受到老師的稱讚,考試還考了第一名。如果晚生個20年,依她的聰明才智和毅力,會不會她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樣了?但人生從來只有曾經而沒有假如,而人生的匆忙也總不允許她停下。
拉拔著一個個孩子長大、結婚、生子,一直到兒孫開枝散葉,但她底心總是因為她而原諒不了自己。那個早夭的第四個孩子,活潑、好動,家裡待不住,總是跟街坊鄰居的孩子玩在一起。有次她不知為什麼發了高燒,那時帶著她急著要去鎮上給醫生看,母女倆沒有交通工具,只能用走的,邊走邊趕著。她擔心醫生要休診了,路上經過了市場一攤賣衣服的攤位,老四看著攤位上的紅色洋裝很是喜歡,央求著她想買,而她一心只想著要快點到醫生那裡去,於是只用打發的語氣跟老四說:「我們先去看醫生,回來經過時再買」。後來醫生是看到了,但再也沒經過那家商店,而老四在之後也走了。
直到80多歲,她說起這段往事時總是忍不住傷心、落淚,後悔著當初為什麼沒買下那件紅色的洋裝。那頂紅色的洋裝彷彿是老四未及的願望,隨著早夭的生命而成為終生的遺憾。後來老三才回想起,在妹妹過世之後不久,她得到了一件新洋裝,而一直要到好久以後,她才知道,那可能是妹妹來不及穿上的那件洋裝。
一輩子節儉的她,惜物愛物,冰箱的飯菜總是冰到不能冰,才讓子女丟掉。巧手的她,對於任何縫紉的活都很在行,就連外孫女家政課要縫的哈士奇大狗玩偶,她也總忍不住技癢,想要不時拿來縫。但每當外孫女要北上回學校、返回工作崗位時,她總是不時會塞食物和紅包給她們,還會叮嚀她們要小心,不要太單純被人家騙,即便外孫女們都快30歲了。
她的慷慨總是留給別人,很少給到自己。在生命的末尾時,住在一天要價超過5,000元的尊榮病房裡,兒女戲稱那是總統套房,這輩子除非子女招待從不可能住五星級飯店的她,在人生的最後日子裡,都還在想著,住在這裡會不會很花錢?子女能陪病的假都請完了,他們要上班該怎麼辦?
直到她離開後,女兒才在她的衣櫃裡,找到之前她去逛菜市場買的全新內衣褲,折得整整齊齊地放在衣櫃下方,或許那時候她想的是,再過幾個月農曆過年時可以穿,但她當時的她也不會知道,她再過幾個月人就在醫院,也沒熬到農曆年,再也穿不到了。
在她的靈堂前,她的國小補校老師也來致意,跟著守靈的子女和孫兒說,阿嬤上課很認真,即便是好久以前的學生,她也記得她上課的神情還有每次都認真寫完交上的作業。
這輩子從沒上過一天班、沒用過社群軟體的她,有好多認識的人來她靈前致意,每個人都可以說上一段跟她的互動,記得她的笑聲,總是有點不好意思地摀著嘴笑的樣子,因為她覺得女生不能笑太大聲,不然很沒氣質。她總是和善地對待每個她碰面的人,也毫不防備地跟每個人在當下交換故事,即便對面那人只是剛好坐公車同程一段的人。
在人生旅程中到站下車的她,總讓身邊的人不禁揣想,如果她不是別人的妻子、母親和阿嬤,她可以有機會是她自己嗎?
留言0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