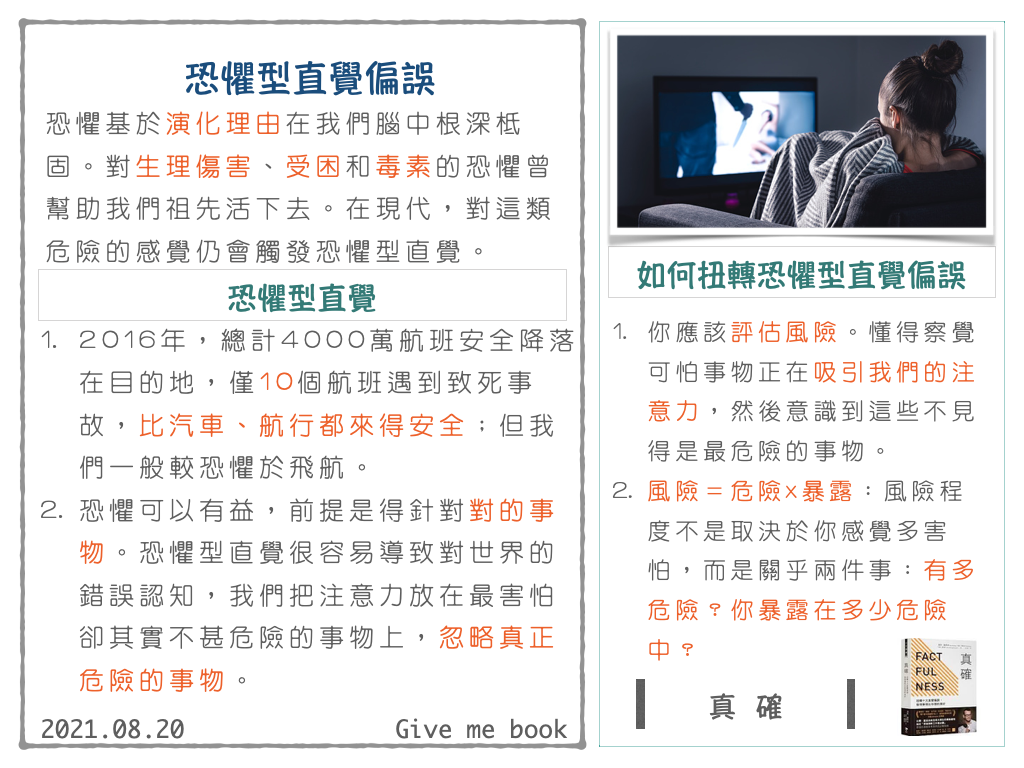作者:陳華夫
我首次認真思考恐懼,是在讀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的這一段:「令人恐懼,比令人愛戴要安全。人民冒犯一個自己愛的人,比冒犯一個自己恐懼的人更肆無忌憚。」當時的直覺,馬基維利比我們歷史裡「賞罰二柄」的韓非子還務實敢講。
我還始終不明白為什麽「恐怖片」會有人看,而且多的是女性觀衆。愈是嚇人才愈賣座。假如觀衆看完說:「也不怎麽害怕!」那才會「嚇」走電影院前排隊的長龍。我不願花錢買罪受,避「恐怖片」而遠之,因此博得膽小之名。但我愛看小說,看的是「文學名著」。有一次讀張愛玲的《金鎖記》,描述的是舊社會女子—曹七巧—的一生,和「鬼」字沾不到一點邊,可是讀到小說結尾處,:「(曹七巧)摸索著腕上的翠玉鐲子,徐徐將那鐲子順著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我一下子毛髮悚然,從心底打了冷顫,這輩子還沒有這麽震驚過。日後讀夏志清教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才發現夏教授說的:「詩和小說裡,最緊張最偉大的一刹那!常會使人引起這種恐怖之感。」(請看你「開悟」了嗎?─開悟的本質(4))
其實,不需「恐怖片」和「文學名著」推波助瀾,這個世界早就充斥著恐懼。「和尚怕念經,學生怕考試」,沒結婚的怕結不了婚,結了婚的人怕遭遺棄。小孩害怕長大的一天不能到來,成年人又怕年老色衰。人們更怕變胖、變醜、車禍、飛機、癌症、黑貓、左眼跳,怕趕掉最後一班高鐵,怕住第「四」樓,怕「鬼」月進醫院,怕黑色禮拜五,怕染新冠肺炎。
可是冷靜地想想,很多恐怖的事情,並不「可怕」。一隻掉在身上的蟑螂會嚇得女孩子大叫,但是蟑螂又能怎麽樣呢?根據「心理學」,恐懼只有象徵的意義。蟑螂只是不幸被選爲恐懼的象徵物件罷了。
恐懼真正的根源是焦慮。生活在競爭激烈的時代裡,人們有著太多的焦慮—即對將發生的事一種持續、模糊的擔憂。仿佛到處都是潛在的敵人,卻又看不見,毫無安全感。於是人們需要一種叫得出名字的恐懼來嚇住自己,以減低擺脫不掉的焦慮。正如「薩特」對希伯來人說的:「假如沒有的話,就塑造一個!」因爲這個世界需要它,世界需要一個替罪的羔羊。於是人們按照自己的焦慮和想像,塑造自己的替罪的羔羊—不管它是蟑螂、老鼠,還是恐怖片,黑色禮拜五。(見拙譯《自我影像─自我心裡探究》陳華夫譯註,1994的第三章)

人們需要恐懼,就找個「可怕」的物件,滿足了恐懼的需要,也因此套牢在恐懼中。其實,世上有哪有真正可怕的事情呢?「死」可怕吧?可是多少人視死如歸。癌症可怕吧?可是多少人和它纏鬥了一生。「沒有恐怖的情境,只有懼怕的人們。」鬼比蟑螂可怕之處,就在沒有人真正見過它。
焦慮是沒法避免,所以恐懼也就如影隨形,時隱時現。但我們卻很少承認自己的恐懼,只嘗試各種辦法去對付它;父母怕孩子爬山出事,就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說:「不是我不讓你去爬山,鍛煉身體當然是很好,就是太花時間。」我們害怕上台演講出醜,卻說: 「我才不愛出這個風頭。」總之,我們是在把恐懼披上「合理化」的外衣。
另一種對付恐懼的辦法是「一醉能解萬千愁」的麻醉自己。尤其今日,鎮定劑泛濫成災,美國醫生經常處方的鎮定劑多達一千四百多種。麻醉自己固然使得恐懼容易捱些,但卻是愈陷愈深,永遠向恐懼豎白旗。
「睡眠」也是麻醉自己的方法。有人一天24小時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睡」,不管是站著或坐著、工作或休息。單純的娛樂也能達成「睡眠」的效果。典型的例子是電動遊戲,「啾…啾…」的按鈕聲混合著「小蜜蜂」粉碎的輓歌,是最現代化的安眠藥。
當然對付恐懼最古老的辦法是迷信。我們先把恐懼染上神秘的色彩,然後採取各式各樣的迷信去對付它。迷信正是恐懼最坦白的招供,比起多方掩飾的「合理化」誠實得多。沒有人真正曉得「十三」爲什麽不吉利,也沒人真正曉得棒球賽和燒香有多少關聯,但是賽前總得膜拜一下。
但是「合理化」、麻醉自己、迷信都沒法真正對付恐懼。恐懼的根源來自焦慮,而克服焦慮之道就在強化、成熟自己的感情,阻止焦慮最好的辦法是令自己「滿意」,不滿意自己的人,對自己、他人及周圍環境有著太高的期望,以致不斷的失望,而衍生了揮之不去的焦慮。這些人總是焦慮的風聲鶴唳,他們在恐懼,在期望最糟的事情發生。就連風吹草動都是「劫數難逃」的兆頭。相反地,滿意自己的人才能樂觀,樂觀才能快樂,快樂正是焦慮及恐懼的特效藥。
多交些朋友,友誼可以使我們享受溫情,樂於合群,而強化了我們的感情。種植草坪是個好譬喻: 若是滿植友誼的花朵,恐懼的野草就無從生根了。
下次,當你正想去看場恐怖片,或是去「網吧」打電動,不妨想一想,你真正需要的也許是:快樂。
請看「陳華夫專欄」─學習的本質─系列文章:
請看「陳華夫專欄」─學習的本質─系列文章:
(
「思考是有意識的系列回憶」理論開啟了思想史革命─學習的本質(1)
什麼是「思考」?如何「洞識」?何謂「思想家」?─學習的本質(2)
什麼是「記憶」?如何「記憶」?「記憶」的本質?─學習的本質(3)
學習的真相與反思─學習的本質(4)
「施捨」就是人生的「現代開悟」─學習的本質(5)
談「恐懼」─學習的本質(6)
探究華人的「罪惡感」?─學習的本質(7)
你孤獨了嗎?─學習的本質(8)
人腦如何創新思考?─學習的本質(9)
「現代開悟」的本質及釋義─學習的本質(10)
你「現代開悟」了嗎?─學習的本質(11)
人工智慧的「強化學習」與人類學習的優劣─學習的本質(12)伽馬波(40赫茲)、記憶、失智症、及音樂治療(2023年版)─學習的本質(13)省思物理科學教育的真相─學習的本質(14)
類智慧真正優於AI電腦圍棋之處為何?─學習的本質(15)細述我親歷40年的學習之旅─學習的本質(16)
AI幫助人們改善記憶、思考能力─適用於年輕與銀髮人─學習的本質(17)
AI徹底改變大學理工教育的面貌─學習的本質(18)
AI模擬人類學習真能比人類更創新嗎?─學習的本質(19)
AI深度學習與《易經》的學習真有差異嗎?─學習的本質(20)
AI之ChatGPT的繪畫審美能力賞析─學習的本質(21)
請看懂智慧的本質:GPT-4的「人工通用智能」(AGI)落後人類有多遠?─學習的本質(22)
臺灣許皓鋐圍棋亞運金牌在學習圍棋上的意義─學習的本質(23)
論才華、機運、及成功─學習的本質(24)
DeepSeek影像生成之有「氣質」、「貴氣」的中國女士─學習的本質(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