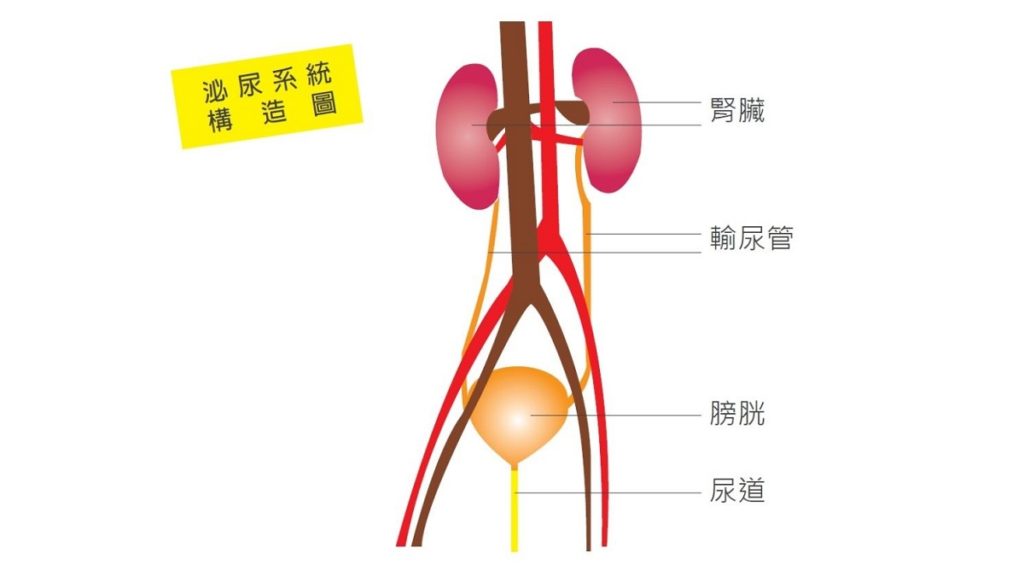感覺流亡:談難民的心理健康問題
從體驗中學習他人對我的膚色、性別、國籍的印象,並且發展出應對的策略,是我搬到歐洲之後開始有的經歷。能夠說英語的亞裔女性究竟代表著什麼,我到今天仍然難以說明。或許是因為,說清楚了這個組群的界定因素,我也等於參與了擘畫這道邊界的工作。而我不願。
因此情況是模糊難明的,圍牆並不清晰,但圍牆存在。一旦說出來那種被用縫隙觀看的感受,那種感受肯定會被否認是來自我直覺連結的理由,混淆我對世事的判斷。
不是每次談話都在訪談,也不必要讓每次交談都像是在為一個更龐大的資料庫收集訊息。事實固然如此,而我經常選擇欠身,選擇道歉,選擇靜默。
我不打算書寫我所在的歐洲,在那裡,我是個異鄉人。我寫作面對讀者,歐洲留在我的私人筆記,在此專欄,我寫我的命題作文。我從未潛心想要認識歐洲,它非我的研究區域,何況翻譯書籍能讀的那麼多,幾乎人人認識歐洲。寫橄欖油寫紅酒寫內戰或者政治角力,這世界對全球之北有莫名的非理性嚮往,有如對全球之南有莫名的同情。人人都想在閱讀經驗中扮演超級英雄,Progressive變成一面獎牌。
偶遇的穆斯林女性
我是個不合格的書寫者,關於英國或者難民遷移局勢。我對當下的社經環境了解不深。我常說,自己仍在識字,儘管這項發展階段不符合我的生理年齡,它徒然引起我的不快。
直覺能夠帶我認識到他們細微的情緒。某一天我讀書心煩,和人應對的事情施展不開,自家花園待膩了,走路去海邊,然後再從海邊走回來。
我家那條上坡路連接主要幹道,幾名穿著罩袍的穆斯林女性正在步行區花圃工作。她們張開雙腿蹲踞的身體姿態在歐洲相當少見,但卻是我熟悉的身體樣貌;在南亞,那樣的姿態是安歇著工作的,代表一種勞動中的自我安頓。女人的皮膚、氣質和身體的形貌看起來像已入中年。
引起我注意的是她們對聲音的敏感。她們聽見一個聲音,那是再過去那家土耳其烤肉餐廳的工作人員在拖垃圾桶。女人揚起臉弓身,臉上遍是警戒的表情,身軀僵硬而花鏟臥在手心,隨時可以反擊。
我不該如何解釋那不是一個普通的表情,是該多虧了我的聯想能力,或者在他人的目光中,那會直接暴露了我過去可能有過相似的經歷。
離散難民群體的生活
在難民研究的課上,老師做了一個實驗。他根據過去在難民營中工作與訪談的經驗,將全班學生分成四組,分別扮演難民的原屬國政府、收容國政府、同種族已經歸化的離散群體、後進待移出的群體。他指導我們四組對話,根據敘述,言說自己在意與需求的事物彼此協商。最後歸納出十五項可能目前的談判與溝通中被忽略的面向。
在對於離散群體生活的描述中,經濟條件的窘迫是明顯的:儘管已經獲得合法居留身份,每週150鎊的薪資付清房租和食物只剩下六分之一。除此之外,惡劣的勞動條件、龐大的債務(為了前往移入地,他們往往必須向親戚或者透過家人向高利貸借款付給仲介)、家中食指浩繁。工作是從清晨6點到午夜12點,女人往往必須待在家照護孩子,或者只能從事時間短、時薪少的工作。在此高壓生活下,生命本身存續的樂趣需要智慧,或者一種對於現狀的無感才能被彰顯。
去感受,成為一種奢侈。
「家中的電話鈴總是紛擾不休,往往是家鄉打來的電話來向我們催討償還借款,或者是催促我們匯寄更多存款好接家鄉的年輕人出來。我開始恐懼電話鈴聲。聽到電話鈴,我只想躲起來。」
我們都害怕談論自己的心理狀態——害怕成為職場上不適任的員工、家庭中不完美的成員、害怕承認在競爭中輸給自己而非他人的實力。治療心理陰影可以像是治療體內發炎或缺乏營養一樣,有具體的療法和可期待的療效嗎?

難民的心理狀態不會在外表顯現,往往最容易被忽略。Photo source : Pixabay
對於難民,談論心理健康是一種奢侈。如何討論心理健康而不使他們,以及我們落入污名套設的陷阱。
在舉著難民可以填補非技術性勞動力缺額的策略性接收政策下,難民最不需要的,可能就是一群醫生來證明他們的身心狀態不適合參與勞動。
貼心的語言往往需要用家鄉話來說。離散群體自身難保,人們往哪兒排遣內在的困頓與悲傷?
政治正確只是一種自保手段,我們誰也不想,被視為是progressive的末流。然而就算是政治正確也未必能夠保證我們正在邁向一個更理解人性更友善環境的新社會。
國家仍然是有效的暴力與稅收總機關。然而,國家的概念過時了嗎?或者,國境為大的概念正要返回我們的日常生活?
是誰,或者什麼能夠填補內心因為離鄉去國失根落難的悲傷?一種新型態的國家?或者烏托邦?
封面圖片來源:wikipedia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