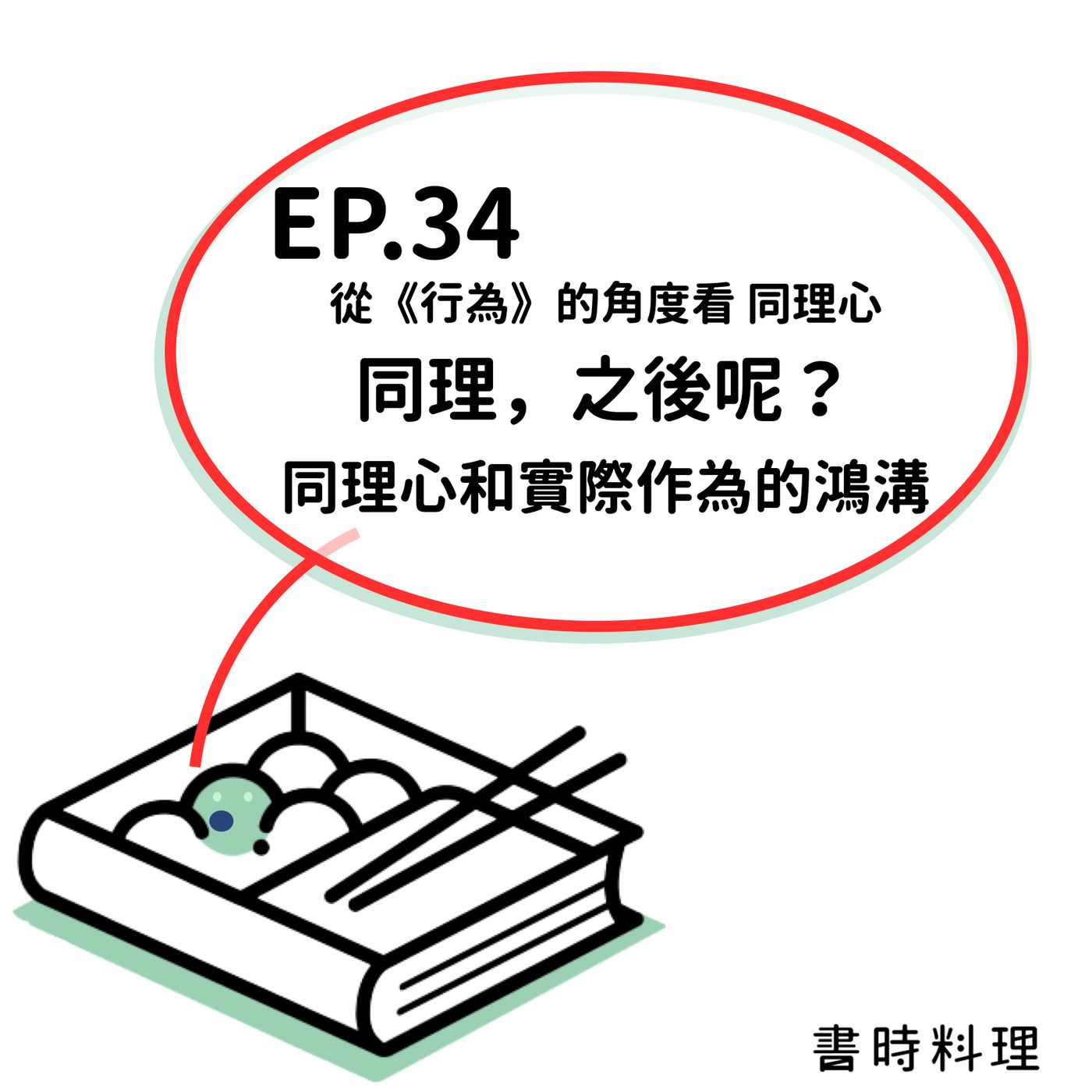從《作為隱喻的建築》談如何讓空間優於時間?

無的遺忘─痕跡
海德格(Heidegger,1889-1976)在喚起「存有」時,什麼依舊被遺忘了?什麼是「遺忘」?死亡是遺忘嗎?德希達(Derrida,1930-2004)說:「我總是力圖使我自己處在哲學思辨的界限上,我說的是界限,而不是死亡,因為我根本不相信今天人們所輕易說的哲學的死亡(而且我不相信有任何事物的簡單死亡,無論著作、人或上帝,特別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凡是死亡的東西都行使著一種特殊的權利)」。
死亡,是徹底的什麼都沒有了,沒了感官經驗、語言、記憶、理性,甚至連遺忘也沒了。遺忘不是死亡,遺忘是如同德希達所說的「痕跡」,德希達以海德格的方法把一個「概念」寫上又隨之抹去,或者直接把「概念」打上一個「X」,以表示這個「概念」是有「歧義」的。如同忘記那曾經經歷過、回憶過、每一次回憶都是重新經歷、都產生不同於前次回憶的那種感覺,原先的經歷並未消逝,只是被時間給「抹去」,但「痕跡」依舊存在。
「痕跡(trace)」是描述「延異(Différance)」的動態過程,痕跡是經過時間的磨損而殘留下來的,它若隱若現,既指向此前的狀態,又指向此後的傾向,卻對自己打上問號。如同文本的書寫是一種意義和詞語在其中不斷被抹去、不斷留下痕跡,其終極目標卻永遠處於變動和不穩定之中的過程。
德希達所謂的痕跡(trace),源於索緒爾(Saussure,1857-1913)的符號學體系,意義並非單獨存在,而是來自系統之內的「差異」。若沒有痕跡、沒有符號系統的差異,我們將無法理解存有;「有」的呈現,是「無」的不呈現,而「有」的呈現也「暗示」了「無」的呈現,只是「無」是以「痕跡」的方式呈現在「有」之中,但它又不是真的呈現,因此,痕跡是滑動在呈現與不呈現(存在與缺在)之間,是語言身上的影子。
痕跡有點相對主義的概念,當我們說某人身高很「高」的時候,暗示了他不矮,我們如何理解、掌握「高」?是在高矮的相對概念中、以及「高」字在文本脈絡間的「差異」,得到此處高的意義不同於薪水很高、高樓大廈、高露潔、高雄、國高中等的「高」。
痕跡是延異的過程,德希達「延異」的發明在試圖瓦解黑格爾辯證法中「時間優於空間、聲音優於形象」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延異無法指涉任何存在的事物、亦無法回到存有(Being)的起源,延異的發明使得無起源的差異思考成為可能。如同寫生,我們看了一眼景物,然後憑藉著我們的記憶畫出眼前的景色,在繪畫的過程中,隨著時間的延宕(defer)與空間的變異(differ)效果便是延異。它永遠不能代表真實,它只能寫出景物的痕跡,因為景物不僅在繪畫的過程中不斷改變、我們的感官也在繪畫中不斷改變。
那麼何謂真理的痕跡?德希達提出「延異」,試圖從真理的痕跡中,找到比真理(邏各斯)更「古老」的東西,德希達稱之為「元書寫(archi-writing)」或「元痕跡」。當然,德希達不會在海德格的存有上打個上一個「X」,因為存有是無法被概念化的,一但我們試圖為它下「定義」,則同時也是存有遺忘的開始。我們如何思考存有?唯有靠「隱喻」來思考存有,隱喻不是概念,若以概念來理解隱喻,那麼隱喻所思考的存有便又滑向以存有者為中心的形上學概念,而這是德希達所反對的(反邏各斯中心主義)。
隱喻的遺忘
概念與隱喻有何不同?隱喻,按《教育部國語辭典》係指以兩物之間的相似性來作間接暗示的比喻。隱喻的成立,來自於兩個條件,一是抽象的問題,另一則在於相似性;抽象需要想像力,相似性需要類比。而概念的成立,則首先是屬性之間的關係,其次是屬性之間的個別特徵。我們如何認識一個概念?如同索敘爾的語言學,首先符號的意義在關係中被認識,其次是個別符號在差異中產生意義。
傳統哲學(特殊形上學)看來,惟有概念化,才能給出意義。因為唯有概念化、邏各斯化,才能在理性、語言、經驗等基礎上被談論。隱喻無法被概念化,因為隱喻是抽象的、相似的,隱喻不是唯一真理的,而是歧異的。我們無法從概念思考隱喻,而存有與隱喻的關係是互相依存,思考存有(普遍形上學)是讓我們重新喚起隱喻的路徑之一,藉著海德格如何思考存有,有助於我們思考隱喻。
海德格存有論的純粹知識(先驗構想力)為純粹直觀與純粹概念的綜合,若隱喻無法用概念思考,那是否表示隱喻便是屬於純粹直觀(純粹時間、純粹空間)的;純粹直觀是感性的、無法用語言描述的、非邏輯的、非經驗的、受納性(receptivity)的。若隱喻屬於純粹直觀,那隱喻便不是概念(符號)的、可被語言表述的、邏輯的、經驗的、自發性(spontaneity)的。但德希達認為:「海德格在喚起存有之時,卻將隱喻再次遺忘於概念之中。」顯然隱喻是比存有更本質的,是更先於邏各斯的二元對立之前的。
德希達說形上學是對隱喻的使用與消耗,隱喻避免不了在概念化過程中漸漸被排擠到邊緣、到遺忘。存有這種「未定」(無、神、X)亦解釋了隱喻本身的不定與豐富,存有本身就是隱喻性的(抽象的、相似的),存有只能用隱喻的方式去思考。如同延異只能使用否定句的方式表示「延異並不是……」,因為當我們說隱喻是什麼的時候,就不是隱喻了、就落入以概念、符號、邏輯思考的邏各斯中心。
隱喻的建築─空間優於時間的可能
神聖羅馬帝國哲學家席勒(F. Schiller,1759-1805)認為:「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日本哲學家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1941-)認為:「建築就像是一邊做一邊修規則並最終成形的遊戲」。遊戲的規則是一種方法論,而不是目的論,遊戲是自由的,並沒有先驗所指,如同德希達的「延異」是沒有本質的,書寫是一種遊戲、在差異系統中的痕跡遊戲。
德希達指出:「藝術和建築是讓解構能夠運作的最有效途徑」、「解構是在對建築本身提出質疑……解構的建築實際上是在拆解建築的基本傳統,並批判任何企圖將建築附屬於其他事物上的作法……是將建築從所有外在的終極性與目標之中解放出來」。
解構的前提是結構,「解構只有在徹底結構化後才成為可能,否則他就會止步於語言遊戲的層面」。隱喻的建築,指得便是用隱喻的方式思考建築,而非用概念、符號、語言、邏輯、理性等思考建築,由此便能問出「究竟為什麼是『有』建築、而非『無』建築?」或「這是否是百分之百無庸置疑的建築」等形上學的問題。建築若作為一種先驗(transcendental),便不是指存有物的建築物,而是指建築的意志(純粹建築)。
何謂建築意志?柄谷行人認為西方哲學是「以建築為隱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即西方哲學話語的高度形式化,既為其他學科的發展奠定地基,同時也宛如建築物向上發展;哲學的發展宛如建築的「巴別塔」,是完整的、系統的、可理解的。「究竟為什麼是『有』建築、而非『無』建築?」海德格稱:「遺忘存有就是對自我差異其本身的遺忘」。海德格所說的遺忘正是指對產生「無」之基礎性、不可確定性、自指性的禁止(例如:我們說存有是無法被定義的,但我們又無法脫離用語言來理解存有)。「無」在邏各斯之前,「無」是對存在者的一切加以充分否定,存在者的一切必須事先被給予,以便將其整個加以否定,然後「 無」本身就會在此否定中呈現出來了。
如何理解『無』的建築意志?便是解構「有」的建築意志,解構建築便是試圖找到建築結構之外的留白、沉默、隱喻,在結構中找到新的、隱喻的空間,並加以重構。如同傳統閱讀與解構閱讀的差別在於,前者是重複性的閱讀(Repetitive Readint),後者是批評性的閱讀(Critical Reading)。解構閱讀拒絕接受文章內容所賦與的表面原始意義與否定其原初的客觀性,而是以批判性、否定性、帶有懷疑的、試圖超越界線的在文本中不斷抹去痕跡的過程。
空間如何優於時間?在海德格的存有論中,空間與時間做為純粹直觀,兩者都「屬於主體」,但時間(internal)比空間(external)以更原初的方式居於主體中,時間優於空間的看法並成為空間的意義,因此時間更是一切任何表象之先驗形式的條件。純粹直觀與純粹概念的雜多必須在純粹時間中透過先驗構想力(the transcendental power of imagination)整理、結合、貫通和發生關係,我們才能夠領會其所形成的知識。空間優於時間的可能性在於─「元建築」;在解構、否定、延異的過程中,「無」的建築意志在自由中綻出了,延異的建築不在時間之中,而在差異中,它消解了起源和歷史,拆解了過去、現在、將來之間的界線。
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說:「一部作品之不朽,並不是因為它把一種意義強加給不同的人,而是因為它向每一個人暗示了不同的意義。」建築之所以不朽,也在於它暗示、啟發了人們的想像力,在不斷解構與重構的過程中,學習解構主義,就是學習豐富、超越自我的想像力,在內部發現新的、隱喻的、無用的、空白的可能,從而在解構的建築、都市、文化中實踐主體生活。
2019/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