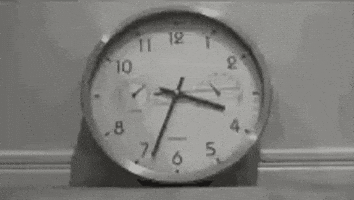1.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撇開玄學成分,這句話其實很符合理學。設想一下,當一個人長期處於不理想的環境中,他的「運勢」自然會隨之走下坡。
比如一個人因為工作疲憊累積多時,日復一日地忍耐,忍著老闆的壓榨,慢慢形成心裡的鬱結,導致整個人的情緒變得易燃易爆。
這種身心俱疲的狀態,自然會讓一個人更容易犯錯,因為疲憊而一不留心,打翻了水杯。因為情緒不滿,導致開車多踩了點油門,導致肇事……
這背後,是我們這一代人普遍的困境。我們身處一個被「內卷」所定義的時代,一種非理性的內部競爭,一種投入與回報不成正比的徒勞消耗。
許多年輕人,包括我自己,都在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職業焦慮中掙扎,我們渴望在工作中找到意義與滿足感,卻又不得不面對經濟下行和競爭白熱化的殘酷現實。
這種深層的矛盾,正是那股將我推向「壞運氣」的暗流。
所謂的「禍不單行」,其實是一條清晰的因果鏈:一個有毒的外部系統,引發了持續的負面內在反應,進而削弱了我們謹慎行動的能力,最終讓「意外」變得不再意外。我的「壞運氣」,不過是這條鏈條上,必然會發生的一次斷裂。
而這一次斷裂,發生在我使用了三年的筆記型電腦上。
週二下午,電腦提示系統更新。我沒有多想,點擊了確認。
進度條緩慢爬行,然後,卡住了。
在那個瞬間,被工作磨損殆盡的耐心讓我做出了一個致命的決定:強制重啟。
這個動作,相當於在一個人的大腦正在進行精密的神經重塑手術時,突然切斷電源。
結果是,我的電腦再也無法正常開機。
我嘗試了所有網路上的自救方法,但都無濟於事。
昨天一早,我抱著它,像抱著一個病危的親人,開始了我的維修之旅。
第一家店的工程師學藝不精,檢測一個小時,打電話叫我換家電試試。
直到第二家店才得到最終判決:重灌系統。
2.
重灌系統後,我抱著電腦回家,開始通過OneDrive、iCloud、微信的手機備份等處,一點點通過雲端上的資料,重新拼湊起電腦原先的樣貌。
在這段時間裡,我想起電影《困在時間裡的父親》(The Father)。
這部由安東尼・霍普金斯主演的電影,以一種驚人的主觀視角,將觀眾完全沉浸在阿茲海默症患者的世界裡。
在老父親安東尼的腦海中,時間是錯亂的,空間是重疊的;女兒的面孔時而熟悉,時而陌生;公寓的佈局在記憶中不斷變換。他對時間掌控感徹底喪失,反覆問著:「現在幾點了?」。
我的處境,正是失智症的數位翻版。硬碟的崩潰,如同大腦中海馬迴的一次物理性損傷。那些儲存的資料,包括過去的照片、隨手的札記、未完成的草稿、數不清的文件,它們構成了我過去數年的數位足跡,我的外接自傳式記憶。
如今,這部分記憶被粗暴地撕裂了。
我努力回想,硬碟裡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東西,腦中卻一片空白。
我知道有些東西失去了,而且很重要,但我無法準確地說出我到底失去了什麼。這種「知道自己遺忘,卻不知道忘了什麼」的狀態,正是安東尼在電影中所經歷的核心痛苦。
我們的時代,個體的「自我」早已不再完整地存於顱腔之內。我們的記憶、我們的身份、我們的社交關係,都高度依賴這些外部的、脆弱的數位義肢。
當這個外接大腦突然「中風」,我們所體驗到的,不僅僅是工具的損壞,而是一種存在性的危機,一種自我的局部死亡。
儲存在OneDrive和iCloud上的資料固然安然無恙,但那些散落在本地硬碟上的,大多是個人的、非工作的檔案,它們隨著硬碟的格式化,灰飛煙滅。
種種看似無心的儲存習慣,不經意間暴露了我潛意識裡對價值的排序。
雲端,那個被我視為永恆、安全、不容有失的聖殿,我供奉的是我的工作。而本地硬碟,那個隨時可能損壞、被我視為次要的凡間,我安置的是我的生活,我的一部分自我。
這不禁讓我問自己一個尖銳的問題:「我是不是,不太重視我自己?」
我對工作的情感,向來是又愛又恨。我熱愛那些能帶來價值感和意義的項目,在投入中獲得巨大的成就感。
但同時,它也像一頭貪婪的巨獸,吞噬著我的時間、精力,甚至是我與自我的連結。
那些深夜不眠的夜晚,我告訴自己是在整理白天的思緒,但或許,那只是用另一種形式的工作,來填補生活的空白。
寫作,本應是抒發,卻也漸漸變成了另一項需要勞心勞力的任務。這次數據的「無意識篩選」,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內在價值的失衡。
那些遺失的檔案,比如一些「無關緊要」卻充滿回憶的瑣碎,它們難道不重要嗎?
它們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但我沒有把它們備份到雲端,這意味著在我的潛意識深處,它們的優先級,遠遠低於一份工作報告或一個項目企劃。
我所遺失的,正是那個被忽略的「關係性自我」的數位殘骸。而我所保全的,則是那個被過度強化的「個體性職業自我」。
3.
這場電腦當機,意外地成為一次對我內心世界的考古。它沒有創造出這個價值排序,而是殘酷地揭示了它。
當我試圖回憶那些遺失的檔案時,我發現自己的記憶是如此模糊、破碎且不可靠。
有些東西,想不起來,就好像從未存在過。這讓我對記憶的本質產生了更深的懷疑。我們常常以為記憶像一台錄影機,忠實地記錄著過去。
但事實上,它更像一位富有創造力的編劇。近年的神經科學研究為這個觀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fMRI的實驗顯示,我們大腦中負責回憶過去和想像未來的神經網絡,存在著驚人的重疊。
無論是回憶真實發生過的事,還是憑空想像一個場景,大腦都在進行一個被稱為「場景建構」的過程。它調動海馬迴等區域,將零散的元素重新組織、建構成一個連貫的畫面。
這意味著,每一次回憶,都是一次再創造。我們所謂的「記憶力好」,很多時候可能只是「編故事」的能力比較強。既然記憶本身就是一種建構,那麼遺忘,或許就不全然是壞事。
事實上,在某些極端情況下,遺忘是一種至關重要的心理保護機制。
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解離性失憶」,它指的是個體在經歷了巨大的創傷或壓力後,會無法回憶起重要的個人資訊。
當現實的痛苦超出了心靈的承受極限時,大腦會選擇性地「封鎖」對這段創傷記憶的提取通道,以此來移除伴隨記憶而來的毀滅性情緒。這是一種深刻的自我保護,讓我們得以在創傷後繼續存活下去。
由此看來,追求一種完美無缺、永不磨損的記憶,本身就是一個迷思,甚至可能是一種詛咒。
如果我們的記憶像硬碟一樣,只會忠實地儲存,而不會創造性地遺忘和重構,我們的人生將會怎樣?
我們將被海量的、未經整理的原始感官數據所淹沒,無法形成連貫的自我故事;我們也將無法擺脫每一次創傷帶來的痛苦,永遠活在最黑暗的時刻。
這次電腦當機,讓我失去了一個外部的、完美的記憶體。但它也讓我重新看見了自己內在那個更古老、更智慧的記憶系統。它懂得取捨,懂得遺忘,懂得如何為了讓我們活下去而重塑過去。
我發現,相比於過去,我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失去」的承受能力,變得強韌了許多。
我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沉溺於損失的痛苦中,而是迅速地思考如何補救,如何讓生活重回正軌。隨著歲月,我漸漸接受失去、挫折、痛苦,並非人生的意外,而是「常態」。
我想起克里希那穆提,他認為能困住我們的,不是環境,而是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思想,在他看來本質上是記憶和過去的反應。我們活在由經驗、知識所構成的連續性之中,因此,我們的生活總是在重複過去,無法體驗到真正的「新」。
我們所堅信不移的,往往只是我們對事實的一種解釋,而這種解釋,可能充滿了偏見和盲點。有時候,我們需要放下解釋,回到最簡單的感受。
我們不必執著於為自己的人生建立一座密不透風的「豐碑」,因為那樣的豐碑,往往是一種被精心挑選、甚至扭曲過的歷史。
要想讓新的事物得以發生,心靈必須從過去的積累中解脫出來,必須有能力「向過去死去」。
這場數據災難,正是一次非自願的、卻極其徹底的「向過去死去」。但當我接納了這個事實,我反而感到一種解脫。
某些看似負面的人生災難,恰恰是我們擺脫慣性、進行真正自我創造的必要前提。在數據的廢墟之上,我第一次感到,失去,也可以是一種自由。
4.
在對於電腦故障,從焦慮、不安到安定的過程,我基本通過「反思」來達到自我安定的作用。
所謂反思,就是「成為自己的傾聽者」。
從事臨床哲學的鷲田清一教授認為,真正傷害我們的,並非痛苦本身,而是「痛苦不被理解的痛苦」。當我們的苦難無法被言說、被聽見時,那種孤立感會讓痛苦加倍。
因此,想要化解內心的痛苦,我們需要認真傾聽自己內心的恐懼,那些深埋在潛意識中、關於自我價值的困惑。
真正的傾聽,意味著不要急著評判,不再急於給出答案,只是單純地與訴說者的感受待在一起。
在我的反思中,我聽見了我的舊故事,它們一部分儲存在那塊失靈的硬碟裡,它隨著數據一同崩塌了。
那個故事或許是關於「努力工作就能成功」。
現在,我需要講一個新的故事。一個成熟的個人物語,就像一個強健的心理免疫系統。
它無法阻止病毒的入侵,但它擁有強大的機制去識別、包容、並最終代謝這些入侵者,從中提取抗體,讓整個系統在下一次面對衝擊時變得更加強大。
最後,我想把我反思的內容轉化成對讀者的提問,提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究竟該如何生活?
我們這個時代,充斥著關於「自我實現」、「活出自己」的口號。這些話語本身沒有錯,但它們很容易被誤解為一種以「自我感覺良好」為最高準則的感覺主義,一種鼓勵個人與世界斷聯的自我中心。
真正的幸福,從來不是來自於對困難的逃避。恰恰相反,它來自於我們如何去處理困難,如何去面對衝突,如何去接納自身的挫敗、脆弱與真實。進而,去重新審視什麼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5.
最終,我的電腦修好了,裝上了全新的系統,乾淨得像初生的嬰兒。那些遺失的數據,大部分終究是回不來了。
但我想,或許這樣也好。因為在這片數據的廢墟之上,我反而有機會,去重建一個更真實、更清醒,也更自由的人生。
失去是常態,衰老是常態,遺忘也是常態。而在這一切無常之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開始,講述我們的新故事。
作者:高浩容。哲學博士、台灣哲學諮商學會(TPCA)監事。著有《小腦袋裝的大哲學》、《心靈馴獸師》等書。課程、講座或其他合作邀約,請來信studiomowe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