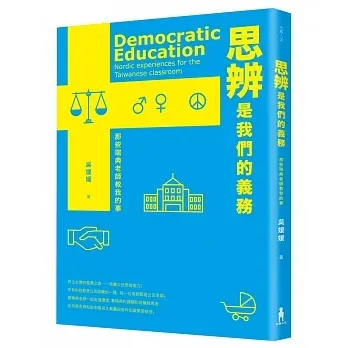我的先生是瑞典高中的歷史和數學老師(在瑞典通常一位高中老師教兩個科目)。有天,我先生在家改歷史考卷,突然哈哈大笑了起來。題目是兩段新約聖經裡的關於耶穌治療病人事蹟的記載,一段從馬可福音中擷取,一段則是馬太福音的片段。
題目說:「根據研究指出,這兩段記載都是在耶穌受難後完成,而馬太福音又比馬可福音晚了約30年。現在請以這個研究結果為出發點,用史料分析的『時間原則』來解釋這兩段記述的異同。」如果學生們理解史料分析原則,應該能以歷史記載的時間點來論述這兩段耶穌事蹟的可信度、相互依賴性、和撰寫人的傾向。
比方說,比較晚寫成的史料雖然離實際歷史事件較遠,但經常有更仔細或誇大的情況,從此可以判斷出撰寫人的目的傾向等等。而有位天兵同學沒好好聽課,最後大概是急了,在考卷上寫了斗大的幾個字:「耶穌怎麼有時間做那麼多事?!」
我笑完以後,不禁感嘆地說,瑞典的歷史教育大概比台灣進步了一光年有吧。我先生聽了,說我給你看個東西。他翻箱倒櫃,找出了幾本泛黃的歷史教科書。原來那是我婆婆50年前上高中時用的歷史課本,裡面還夾著幾張考卷。我看了那些課文和考題,一個個帝王偉人和戰事的排列,一道道條約和年代的填充題,和我在台灣學的歷史課風格大同小異。
五零年代後半是瑞典歷史教育改革開始向中學滲透的時期。我婆婆上大學後主修歷史,她記得一次在課堂上,教授一邊發回她們的歷史報告,一邊發火大罵瑞典高中的歷史教育,把瑞典公民教成了愣頭愣腦的書呆子。那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學界開始提倡改革,但是接受傳統教育,已經使用傳統教學多年的高中教師們還在舒適圈徘徊。那位發火的教授召集了其他學者們擬定了一套課綱,還編了一套歷史教科書,那套新的教科書問世後好幾年都沒被歷史教師協會採用。
但是,這個滲透的力量不容小覷。當新一代的教育決策者和歷史教師慢慢被育成,改革的風氣很快就席捲了瑞典中學。才事隔一代,我先生看著他媽媽學過的歷史課本,都覺得不可置信。
瑞典中學的課堂實驗
教育是台灣人心中的痛。我永遠忘不了自己青春正盛的那幾年,一天天過著補習考試枯燥的日子,唯一提醒我一週又過去的信號就是抽屜裡又滿出來的考卷。這種教育從我爸媽那一代開始,經過我們,現在眼睜睜看著我們的下一代也排著隊走進這條不歸路,相信為人父母長輩的都為他們感到無奈和心疼。那些為了改善聯考壓力的教改政策,不但沒有改善學生的壓力,甚至更助長了填鴨和補教產業的欣欣向榮。
對於台灣升學壓力的來源和結構,我認為有必要做更深入的分析。其實在歐美的學校裡,那些想要追求學術卓越的孩子們,也承擔了不小的壓力。為了進入競爭較激烈的大學科系,瑞典的高中生也必須挑燈夜讀。我先生說在他工作的學校,每次舉行全國考試,一定至少會有一位學生考到一半開始啜泣,還有一位會吐在考卷上。所以考試壓力,在世界上每一個學校都是不可避免的。台灣教育的問題癥結,就我個人的淺見,是在於兩點:第一,追求學術卓越的壓力被普遍施加於每一位學生,一個孩子的價值完全被其學術表現所左右;第二,教學內容的僵化和脫節。我想試著以我對瑞典高中教育的一些瞭解,反思台灣教育的這兩個問題。
首先,我想從教學內容談起。現在台灣的教改把重心放在升學制度,對真正應該大改特改的教學內容和方式卻換湯不換藥,導致我們的學子每天花費漫長寶貴的時間記誦演算,但思辯批判能力仍然低落。其實這點我不是不能理解,在台灣,無論家長、老師、教育決策者都已經在填鴨式教育的舒適圈裡面待了幾個世代,就像五十年前的瑞典歷史老師一樣,要走出來真的不容易。

Photo source : wikipedia@Public Domain
我來瑞典以前,只聽說西方的教育和台灣很不一樣,但是怎麼不一樣,我沒有概念,連描繪一個想像圖都很難。所以我想藉這個機會,給大家說幾個瑞典中等教育有趣的例子,希望能大致呈現思辯性教學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成果的全貌。
剛開始在瑞典的大學教中文的時候,學校給我60個小時上教學法課程。我那時候已經開始教課,心裡想,還不就是照著課本教,有什麼好上的?但這是學校規定,而且上課還可以領薪水,何樂而不為?我和其他同事拿著鉛筆盒和筆記本,又當起了學生。前半部課程我們先站在學習者的角度,去瞭解人類各種學習的機制,後半部課程我們才站在教師的角度,去討論我們在學校課堂的環境裡如何去促進最有效的學習。經過了這門課,我才瞭解教育這個領域的深度,也觀察到瑞典和歐洲同事對教育學的尊重和涉獵。相對於自己對教育學的無知和輕慢,讓我十分汗顏。
在教學法的第一堂課,教授就問我們,什麼是老師?什麼是教育?他問到我的時候,我馬上運用以前背得滾瓜爛熟的韓愈師說回答:「老師就是傳授學問的人。」這時候教授又問我,什麼是學問,學問在哪裡?我搖搖頭,答不上來。
上完這門課,我得到最大的體悟是:在傳統的教學理念中,教學是老師把學問灌輸給學生的過程,老師先把客觀世界都吸收轉化成了特定的知識,然後餵給嗷嗷待哺的學子,目的是讓學生更博學多聞。啟蒙時代以後的教育理念裡,老師並不是學問的載體,更像是一個引導人,老師和學生們一起站在客觀世界的前面,引導學生和世界接觸,產生激盪,藉以養成學生自主探索新事物的習慣,和培養能理性分析資訊的批判力。這個引導的過程看似放任輕鬆,其實需要很強的專業和教育知識為後盾,加上精心的設計和安排才能實現。
我們上最後一堂課的時候,教授說我們來玩個問答遊戲。他開始問我們「挪威的首都在哪裡?」「瑞典最長的河是哪一條?」「歐洲最高峰是哪一座山?」一問一答,大家都搶著在第一時間說出答案。最後他問「為什麼瑞典的首都在斯德哥爾摩?」這時整個教室突然安靜了下來,大家都半張著嘴,腦袋高速運轉著。教授笑著說:
請你們記住現在這個感覺。我們學了很多理論,討論了很多教學法的學術研究,希望你們以後慢慢吸收應用。但是從今天起你們可以開始落實的,就是記得剛剛那種一時半刻找不到正確答案的感覺,你們要讓學生常常處在那樣的狀態!
你們的教育聽起來「很便宜」
那天回到辦公室,我看著自己為中文課做的教案,突然看到了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就這樣,我在自己的課程裡進行了一個小小的教改。
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會覺得,引導學生和知識激盪,培養思辯能力的教育,聽起來很棒,但是這種教育在台灣實行的可行度有多大?培養這樣的學生對於台灣社會又有什麼實際的效用呢?
記得有天我和我先生的同事們聊到了不同國家的中學教育,我形容了我在台灣的經歷:一個老師教40位學生,教學以講課的方式為主,評量則多採取可以快速評分的選擇和填充題。一個瑞典老師聽了以後說:「你們的教育聽起來很便宜,可以替政府省不少錢。」我聽了一愣。我聽過很多描述台灣教育的形容詞,但是「便宜」這個詞,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後來我細想,可不是嗎?原來我們的教育,就是最省錢的那種!我以前曾經認為,注重考試是牽制台灣教育的主因,為了達到考試的公正性,我們不得不採用記憶性的、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題目,這也導致了比較死板的教學內容。然而,看了歐洲幾個國家的考試題目以後我發現,思辯性的能力絕對可以用公正的考題來評量,只是這些考題的設計和批改都要花費十分龐大的資源和精力罷了。當過老師的都知道,出一道記憶性的題目只要20秒,但是出一道思辨性的題目,可能要花上幾個小時。
台灣一位中學老師要帶近40個學生,上課時要趕進度,幫學生準備考試,課間還要照顧輔導學生心理、家庭的種種問題,下班以後來自家長的叮嚀更讓他們不堪其擾。在這種條件下,要如何設計吃力又不討好的教案和考題?
學會如何去「質疑」
瑞典高中每次上課的學生人數大約是25人。另外每位老師會分配到大約20個「導師學生」,導師和學生定期見面,聊聊生活和學習上的種種。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導師察覺了更深刻的家庭、心理,或學習障礙問題,學校另有專業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師、特教老師提供協助,也和社福機構緊密合作。
我先生前陣子把一個在家庭方面有很多煩惱的學生,交給了學校和藹的諮詢師。他的專業不在心理諮詢,幫不上忙,也沒人覺得他應該幫忙。相反的,他和另一位數學老師,每個禮拜一放學後在教室門口掛上「數學急診室」的布條,照顧那些因為數學而身心受創的孩子。那才是他想做,也真的有能力做的。
除了減低師生比,和讓老師能更專注於各科的教學之外,瑞典各機構也致力於協助老師設計教案和考題。比方說瑞典高中歷史第一級,有一個學習目標是習得歐洲歷史幾個重要的時代劃分,如佃農時代,海權時代,啟蒙時代等等,學生必須學習這些時代的特徵,並且理解各時代是用什麼視角去劃分的。最後,學生必須去「質疑」(Problematization)一個「時代」概念的形成。
就這一點,教育部提供了「維京時代」作為示範教案,建議老師可以問學生,對他們來說「維京」是什麼,他們覺不覺得自己是「維京人」?接著老師可以解釋,「維京時代」這個詞彙其實一直沒有很受重視,直到19世紀,那時德意志和義大利統一運動正如火如荼,斯堪地納維亞(Scandinavia)國家也產生了政治合作意向和尋找共同文化和歷史背景的需求,維京時代和文化突然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

斯堪地納維亞。Photo source : 公有領域
這時老師可以請學生想一想,一個歷史用詞的生成,和當時的背景有什麼關係?從這個「質疑」的過程中,學生可以去思考歷史知識的人造性,以及歷史和建構「我們」和「他們」這種群體意識的緊密關係。如果對教學法研究有興趣,高中老師可以申請成為「創新老師」,學校給「創新老師」很多時間和空間去發展更好的教案,薪水也更高。
以上提到的這幾點,無論是協助設計教案和考題,確保小班制促進討論風氣,或是尊重老師的專業,讓老師能專注於各科教學等等作法,都勢必要國家不惜投入資源和經費。我查了一下不同國家在中等教育支出的經費,台灣中等學校「每生使用教育經費占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之比率」大約比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少了25~30個百分點。台灣絕對不乏優秀的教育學者,願意求新求變的學校教師也不在少數;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我們總是念著國外教育的好處,想必台灣的教育者聽了也是很心酸。
台灣的教甄考題裡有一題是這樣的,現在台灣高中一個班級的平均學生人數是多少?答案是,目前公立學校每班平均為35個,私立為40個,而私立學校一班有比較多學生的原因是「更符合成本」。我也看過一個報導說,因為台灣少子化趨勢,將會造成老師市場的緊縮,導致老師失業。少子化在很多國家是步入小班制的契機,在台灣卻變成了老師的危機?說穿了,還是那一句:「要符合成本」。
所以,要促進教學內容的思辯化,提升教育品質,作法細節林林總總,但是最後一定都會回到資金問題來。總歸一句:便宜沒好貨,教育也不例外。那錢從哪裡來呢?經費的分配固然重要,但是在那之前,先讓我們增加台灣那和斯里蘭卡不相上下,少得可憐的稅基吧!一提到繳稅,想必很多人開始躊躇了。別擔心,台灣目前的稅收之所以會這麼低,問題不是出在我們全體人民繳的稅不夠,而是稅制的不公平。
台灣是世界上碩果僅存數一數二優待富人和資方的民主國家,我們不需要把眼光放到瑞典或德國,光是能趕上日韓水準,就是一大進步了。台灣的稅制怎麼會落得這般田地,那是往事已矣,今後積極改善才是正途。大選將近,「稅制改革」這四個字是最好的照妖鏡。在這面照妖鏡的法力下,藍藍綠綠,牛頭馬面,全部都無所遁形。希望為人父母師長的看清楚看仔細,為了台灣的下一代,投下明智的一票。
從不同視角詮釋的法國大革命
回到課綱和教案。為了達到學習目標,除了各機關提供的示範教案以外,每個老師也能配合自己設計的教案,用不同的視角去詮釋。比方說在教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其中一項學習目標是「理解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社會摒棄非理性傳統的風潮。思考這些革新的意義和成敗。」對於這點,一個很普遍的示範教案是讓學生討論傳統節日的存在意義,思考那時在法國為什麼很多人反對過聖誕節。
身為數學老師,我先生則選擇了以公制單位的推行為例,來引導課堂的討論。法國大革命時期,有鑑於各種文化中傳統測量單位的非理性和不統一,法國科學家制定了現在大家熟知的公制單位,這種單位用地球從北極到赤道距離的千萬分之一為一公尺,並以水為基準,把長度計量和容量、重量等連結在一起。這個當時最「理性」「革新」的度量衡單位,除了美國等少數國家以外,幾乎被所有國家採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實那時候法國也推行了時間的十進制單位,一天為十小時,一小時為一百分鐘,但是這個革新在推行期間並沒有真正普及,而且幾年後就廢止了。
在課堂上,學生們爭著發言討論為什麼度量衡的革新被採用,時間的革新卻失敗了?有個學生說,一個小時一百分鐘,我光聽就累了。還有學生說,不知道時間的革新對鐘錶業的人來說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我自己在聽這些趣味橫生的歷史時,彷彿感受到了兩百多年前法國社會的氣象,對於他們積極審視傳統的那股傻勁,在莞爾的同時,也感到肅然起敬。平平是法國大革命,在瑞典課堂和在台灣課堂裡學到的,竟然可以如此不同。

法國七月革命。Photo source : wikipedia
剛好在數學第一級的課綱裡,也有一個學習目標是「質疑生活周遭數學單位的習慣用法,理解這些單位和歷史和物質環境的關係」。比方說世界上很多文化之所以採用十進位,不是因為十這個數字在數學上有特殊意義,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十根手指頭。電腦沒有手指,它們只認得電路,所以我們用二進位或十六進位和它們溝通。法國大革命期間,人們覺得源自於腳掌大小或是石塊重量的傳統單位已經不合時宜,運用人類對地球和自然的新知識,整合出一套更簡便、更理性的度量,這個單位現在已經被大多國家的人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學生必須理解,所有的度量都是人造的,只是一種約定俗成,我們可以用巴比倫的十二進位,用英呎或公尺,那只是演算上的改變;而數學的本質,客觀物體的本質,並不會因此而改變。這個近乎哲理的學習目標,被安排在瑞典最初級的高中數學課綱裡;我雖然閉著眼睛都能解二次方程式,卻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些饒富趣味的問題。
綜觀瑞典高中的課綱安排,會發現他們每學完什麼,都一定要「質疑」一下;另外,他們傾向把比較抽象的、偏向哲理性的學習目標放在初級的課綱裡。我想這是因為很多科目的中級,高級課程並不是必修的。許多學生可能學不到進階的三角函數和微積分,但是,數學的意義、數學和人類生活的關係,是所有學生都應該試著去咀嚼和領略的。
瑞典高中文史科課綱的柔軟度,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與其規定老師必須要教哪些史實、哪些文學作品,課綱中的學習目標如以上舉的例子,更以培養解讀技能為主。在細節上,老師可以發揮一定的自由。這除了是那位發火的歷史教授改革的成果以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原因——瑞典的課綱,是國會中所有政黨一起審視和妥協而成的。
他們瞭解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對塑成一個人群體、政治意識有太大的影響力,所以最後妥協的方案,就是所有政黨都不要想主導歷史文化的代言權。取而代之的是授予學生解讀歷史、文本的工具和視角(perspective),讓學生能獨立判斷。因為這一點,瑞典也省得像台灣一樣,每逢改朝換代之際就要發生「課綱微調」的問題。
到底什麼是課綱?而什麼樣的課綱,是台灣最需要的呢?這就又回到了另一個主題:「我們不惜投入資源經費,讓引導式、思辯性的教育成為可能,到底對台灣社會能達到什麼實際影響和效用?」
另外,在台灣教育體系還偏僵化的現實下,身為現場教育者,可以開始做些什麼?台灣社會期待每一個孩子都去追求學術卓越的心理根源是什麼?又能如何改變呢?礙於篇幅,留待下次繼續。
封面圖片來源:wikipedia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