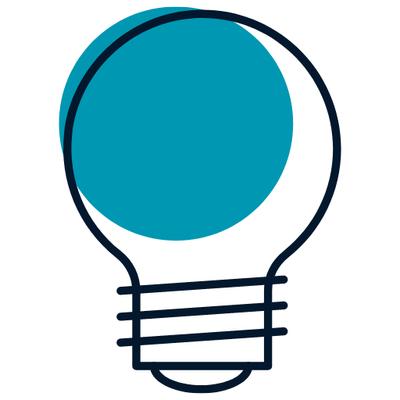〈開會是為了一同前進:避免冗長會議、回歸協力的夥伴關係〉2025-02-16
從小學學英文的時候,就一直覺得「company」這個詞很有趣,它既是「公司」的意思,又可以用來表示「陪伴」,一個很簡單的想法是:公司就是一群夥伴待在一起。尤其在沒有實際出社會工作過的小學生看來,這聽起來沒有什麼違和的地方。
從我查到的詞語歷史來看,這個字源自拉丁文「companio」,意思是「一起吃麵包的人」,用來指旅途或生活中的夥伴。之後演變為中古法語「compagnie」,開始用來形容一群人(尤其是軍隊或商業團體)聚在一起,之後才被英語借去,逐漸發展出我們現在的「公司」用法。
這個詞的歷史,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如今商業公司的「前世今生」。這個詞所指代的夥伴規模變得比以前要大,能做到更多無法只靠少數人就做到的事;另一方面,夥伴間的情感似乎也就不像舊時候那麼密切,比起「一起吃飯」,更像是一起餬口飯吃。
*
而為了要把事情做好,一群人就需要開會。而「會議」,剛好又是另一個讓兒時學習英文的我們感到有趣的詞彙,因為Meeting顯然是從meet(遇見/見面)來的。而且這個關聯不僅僅存在於英文或與其密切相關的語系,在中文裡,會議的「會」字,也與「會面」的意涵脫不了關係。於是「一群一起吃麵包的夥伴會面」,在我們這個時代成了公司開會的意思。
然而,在我們實際經歷過一些「開會」之後,多數人並不會感覺像「一起吃麵包」那麼輕鬆。就算真的是邊吃東西邊開會,我們還是經常會感到冗長、煩悶,一場會議下來,經常感覺明明還沒具體完成什麼,就已經精疲力竭。
之所以會有這種感覺,不外乎有幾個原因:會議時間過長讓人難以專注,議程不清導致討論失焦,甚至有些與自己無關或無從置喙的部分卻仍需強制參與……。如果每週、甚至每天需要開這樣子的會議,再大的熱情,也很難不被一點點消磨殆盡。
但在另一方面,這個時代的「事情」的規模就是愈來愈難單靠一個人或少數人去完成,我們無可避免需要在職業上面與其他人合作。需要與他人一起處理複雜的難題、透過眾人的不同專長與腦力激盪,找出單靠自己無法給出的解決辦法。
於是,思考如何讓會議聚焦,不要變成事倍功半的「冗會」成為了這個時代裡面至關重要的問題。
*
我認為,要解決會議冗長不聚焦的關鍵是:不要把會議當成一件「事」,不要為它預留一大段時間、也不要叫大家都去開會。而是,讓這些會議回到其溝通的根本目的。我們是為了做到某些事才開會,那就只處理那些事,也只請那些跟這些事有直接關係的人來開會,再將結果轉達給其他次相關的人。
為了要做到這點,我們應該在開會之前就明白地讓所有人知道這個會議屬於哪一種會議,譬如是「公告分配型」、「進度回報型」、「腦力激盪型」還是「決策型」。那些冗長且沒有重點的會議,常常就是把這四類事情(乃至於更多不相干的事情)放在同一場會議裡面討論。於是可能會出現,要做決策時,有人還不知道之前發生過什麼事,又或者後面才公布的情況,直接推翻了前面討論的事情。這是開會之前就應該要避免的。
一旦確定了會議的種類後,我們還需要把會議的時間與人數做紮實的限定。譬如說半小時或一小時內要結束會議、「兩個披薩」以下的參與人數。如果擔心這樣的時間會討論不完,那很可能是因為原來的設定就不夠聚焦,把應該要分成多個細項的任務未經整理就丟進會議中,應該要由負責主辦這場會議的人把重點先釐清出來,而不是讓所有人一起在失焦的討論中迷航。
只要當每個人都能夠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溝通,而不是彼此消耗、厭倦或應付會議,才有可能像是「旅途中一起吃麵包的夥伴」那樣,真正朝同一個方向一起前進。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