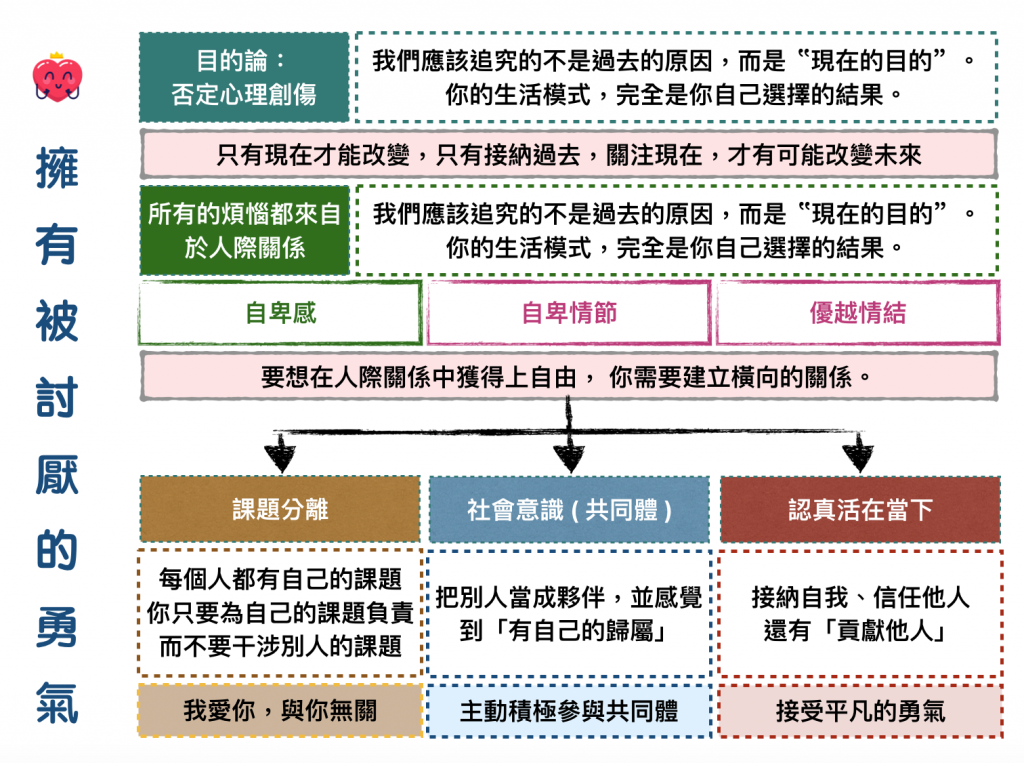《被討厭的勇氣》(下):否定「否定心理創傷」之後的肉身經驗理解
在〈《被討厭的勇氣》(上):「否定心理創傷」是一種邏輯語言的暴力〉中,我們談到哲學家的目的論背後隱含的邏輯語言世界觀,暴力地以單一看待世界的框架,將我們的肉身經驗排擠在外。然而在否定哲學家的「否定心理創傷」之後,我們該如何重新理解心理創傷?如何重新將此類科學和邏輯語言無法描述的真實肉身經驗拉回到我們的生命之中?既然是企圖將經驗與個人生命關連起來,讓我們從時間開始。

線性的「過去-現在-未來」是常見的對時間的理解,也是書中年輕人和哲學家的錯誤預設。年輕人之所以主張「人不能改變」,是認為現在的我是從過去走來的,是過去造就了現在的我,而來自過去的心理創傷,也造就了現在的我是無法出門的。過去無法改變,所以現在的我亦是無法改變的。
這種因果論以一種單向朝向過去的視角來理解現在,難以避免哲學家所說的宿命論。現在的我變成由過去經驗累積起來的無機物,我凝視面前一堆時間穿透我而遺留下來的過去經驗,我只用它們來解釋自己,好似時間推著我走,把我變成這樣或那樣。至於未來,它是沒有意義的,未來只是一個尚未到來的現在,於是我倒退走,背對未來前進。
另一方面,目的論的時間觀則認為我們是面向未來前進的,我之所以是現在的我,是因為受到未來的引力吸引,我帶著目的行動,一併地形塑自己。那麼過去呢?它只是曾經的現在和未來。
既然因果論的時間觀導致悲觀的宿命論,那麼換個方向凝視的目的論為什麼又有問題?問題就在於它只是同一個線性時間軸上的轉向。目的論和因果論就像是孿生姊妹,兩者同樣佔在現在,一個拋棄過去、另一個丟棄未來。然而朝向未來並不能保住改變,它只存在於形上學世界,碰到現實,我們都知道,未來是不能夠同化成眼前的東西的。未來永遠未知、永遠無法抵達,所以哲學家的目的論要我們為一個不知道的、無法承擔的東西負責,是不折不扣的暴力。
所以關於時間,我們可以從能夠碰觸到的現實、可以負起責任的現在來理解。再一次地,我們看到生活的虛無所展開的此刻時間的Horizon,擺脫線性時間上的現在,把當下佔據的時間稱呼為此刻。此刻是被過去環繞的空白中心,它被無數個過去凝視,從而保證了自身的存在,它being-for-Other以還原自身。同時,它也因為意向弧的張力,箭在弦上、蓄勢待發,但是我們看不到那個要轉彎之後才得以看見的未來。如果說此刻是在中心的空白,那麼我們的肉身經驗(如心理創傷)要安放在哪裡呢?答案就在無數個可以凝視此刻的過去之中。
此刻時間被多個不同視角穿透,過去不只有心理創傷,還有其他許許多多,此刻不應該只有無法出門這個唯一可能,更不應該線性的延續到未來。拋棄掉線性的時間觀,我們不再是走鋼索的人。
反過來看,此刻的我們被無數個經驗環繞,時間是空間性的,我們棲居於時間之中,一邊築造一邊維護屬於個人生命的家。時間也是肉身化的,我們安放肉身經驗,活得立體、安身立命。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