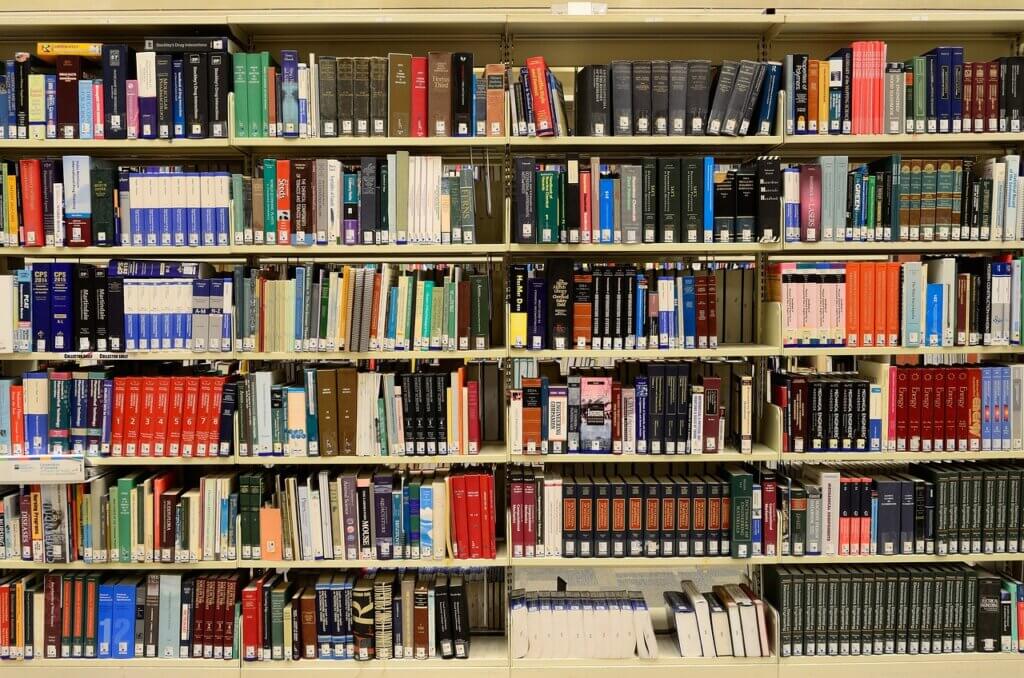〈《誰偷走了你的專注力?》閱讀筆記(三):閱讀能力、注意力與同理能力的缺失〉2024-12-28
在普羅威斯頓的西區有一間舊書店,專程到普鎮進行「數位排毒」的海利幾乎每隔一天就會到書店裡晃晃、買本書來讀。他看見收銀台工作的店員經常在讀書,而且每一次,讀的都是不同的書。海利在閒聊的過程中提及對方書讀得很快的事,店員卻說,其實她只能讀得下每本書的前一兩章:「我想我無法集中精神。」她說。
海利知道這不是那名店員個人的問題,甚至連他認識的一名書評家也和他說過類似的事。就連這些與書籍為伍的人都感受到自己無法長時間閱讀,在更一般性的大眾裡面,這個問題只可能更加嚴重。
根據著名民調公司蓋洛普(Gallup)的調查,自1978到2014年,全美「一年之中一本書都沒讀過」的人數比例成長到原來的三倍。到了2017年,每個人平均每天花在看書上的時間有17分鐘,滑手機的時間則是5.4小時--這個差距如今很可能已經變得更懸殊。人們不再為了消遣、打發時間或學習新知而閱讀,透過螢幕,我們動動手指完成這一切。
二十多年來持續追蹤人們閱讀習慣的學者安納.曼根(Anne Mangen)指出,螢幕閱讀是一種與書本閱讀很不一樣的方式。在閱讀螢幕上的文字時,我們更可能用掃描、略讀的方式,快速地從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而不會像傳統的閱讀那樣專注與沉浸。海利將其譬喻為「在生意很好的超市裡跑來跑去,搶自己需要的東西」。
閱讀變得不那麼吸引人,也不那麼深刻。在這本書寫就的時候,就已經有至少數十項研究指出存在有「螢幕劣勢」,無論是成年人還是學童,透過螢幕來獲取的資訊會更難被記住,對那些資訊的理解也會明顯地更差。
當人們失去閱讀長文本(與較難文本)的能力時,他們的注意力也會變差;而一旦他們的注意力變得更差,就更無法靜下心來,好好捧著一本書進行深度閱讀。海利意識到,這與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談及電視改變人們看到世界的方式時說的是相似的事情。當我們生活中的主要媒體改變,那不只意味著我們接收資訊的方式與管道改變了,我們就像戴上了一種新的護目鏡,眼中的世界將完全不同。
*
在我看來,透過書本閱讀和透過螢幕接收,就像演繹推論與歸納推論那樣迥異。當我們閱讀書本,我們是一字一句、一行一行讀下來,如果這句話卡住了,就無法推進到下一句;但在螢幕上,我們快速地瀏覽過去,被動地讓關鍵字從字裡行間中浮現出來。
只有當我們「感覺」這篇文章和我們原來的立場相近,或者對我們「有用」,我們才會擴張我們的注意力,展開那些我們感興趣的部分來讀。其他時候,滑掉它,就像在擁擠大街上繞開路過的陌生人一樣。
而這種閱讀文字能力的缺失,也讓人更難擁有同理心。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教授雷蒙.馬(Raymond Mar)指出了另一類「閱讀影響思考方式」的情況。雷蒙透過「認識小說家與作家的名字與否」,將受試者分為了讀小說的人、讀非小說書籍的人和不怎麼讀書的人。
他的研究發現,讀小說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同理心、更加擅長閱讀與理解社交訊號。雷蒙的研究認為,閱讀和單純的接收資訊或單純的想像都不同,「我們的注意力位於非常獨特之處,先向外(頁面、文字),然後向內(文字代表的內容)波動。」
在雷蒙的研究中,非小說的書籍在這方面的效果有限,長篇影集的觀眾則會得到相似的提升。但短的節目對此基本沒有貢獻(當然,滑短影音更加無法增加我們的同理能力)。
當然,雷蒙自己也知道自己實驗設計可能有問題的地方,他指出,相同的結果也可以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讀,也可能是「有同理心的人更容易被小說(長影集)吸引」。但雷蒙相信,很可能這兩者都是真的,就像前面說的注意力缺失與閱讀能力下降的循環,同理心上升與閱讀長篇故事能力的培養,也很可能是一種值得我們追求的正向循環。
雖然看起來可能沒有那麼直覺,但只要細想就能明白,為什麼同理心與專注力會如此息息相關。因為「設身處地」這個行為,首先要求「那裡有一個完整的、真實的世界」,我們才可能投入進去,去理解對方的感受。這是匆匆略讀的資訊吸收模式無法提供、甚至完全反對的。
就像我們曾經提過的,現今許多網站與app的設計,就是為了讓你分心而存在。他們沒有要讓我們專注地投入的一個特定的世界裡面,他們將一切切割成強烈的情緒碎片。一下子要你大笑、一下子要你義憤填膺。滑一整天短影音和社群媒體的人很可能說不出自己到底看了什麼,但什麼情緒都經歷了一輪,而且對自己周遭的事情感到麻木,畢竟,它們怎麼可能像螢幕裡發生的事情那樣辛辣有趣?
當人們快速地失去專注與同理的能力,無法從文字看到另一個人生命的重量時,他人的苦難不過是一場再無聊不過的老掉牙故事--「又是政治正確那一套」,他們理解不了(也意識不到這種理解能力的缺失是自身的問題),卻說著無數自以為幽默的嘲笑。這是我們所處時代的悲劇。
前篇: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