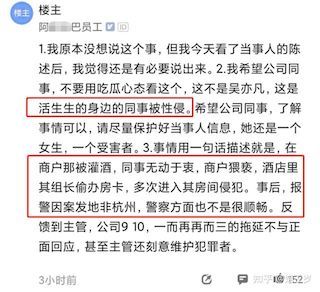性侵—永不抹滅的痛痕 (上)
那一天,我逃出來之後,
等待我的是永無止境的惡夢與一輩子痛痕。
一個人面容憔悴的走到警察局,
身上衣物破爛不堪,體內流著賤男的精液,
面對警察的詢問我低頭不語,默默的痛哭流涕。
人渣淫蕩的表情、侵犯我時的粗暴、泯滅人性的暴力、強迫滿足性器官的威嚇,以及下體不斷被撕裂的劇痛感,使我每天痛不欲生。
為了不讓我懷孕,有時會挑我的安全期,
有時只是冷冷地丟一盒藥叫我吃下去,那個人只是為了自己的爽而踐踏我。
我什麼都反抗不了,每天必須要靠那個人給我食物活下去,家裡的危險物品、聯繫外界的手段都被收起來了,防止我自殺和逃跑。
更甚至,我身為人的存在意義,
彷彿從一開始就不曾存在過,是個沒自由的性奴。
我已經不曉得,像這樣的人生究竟有何意義?
在本該快快樂樂長大的童年,沾染上永不抹滅的痛痕,我做錯什麼了?
日復一日的惡夢,回想起來就猶如昨天剛發生一樣,漸漸的我放棄生存的意念了。
我流淌著人渣父親的血,我是一個骯髒的賤人,
從出生起即是惡夢的開端。
在那漫長的童年裡,陪伴我的是父親的作嘔嘴臉,
我既沒有家庭的溫暖,也沒有親情的愛。
「眼淚...?我早就已經哭乾了」
我哭著求過父親不要這樣對我,
因為我下體真的好痛好痛,然而換來的只是無情的一巴掌。
那疼痛感使我驚呆住了,
稍有服侍不好就遭來辱罵和歐打,
只要我「不乖」就會受到肢體暴力。
「......」
好多年過去了,在我逃出來後,接受了很多偵訊,每當詢問時都要想起父親那恐怖的模樣,逼迫我去回想這不堪的記憶。
出庭作證時,雖然沒有與加害人直面,但我仍然很害怕,因為那個人渣就離我不遠處,我強忍淚水煎熬的回答法官問題。
沒有具體的描述經過,法官不會採信我的證詞,對方的律師百計千心的辯護,只為了讓結果「逆轉」,甚至讓刑期盡可能的降低。
我憤恨又難過,雙手緊緊握拳,明明做錯事的畜生就在不遠處,我要一邊忍受隨時崩潰的情緒,一邊看著對方不停辯護的律師,千方百計的打擊阻撓我。
我怒不可遏的死死盯著前方,又輪到我發言時,我終於止不住情緒了:
「請把我正常的人生還給我啊啊啊啊!!!」
那一刻全場安靜了許久,或許是感受到我的憤怒悲痛,就連法官和書記官也罕見的面露難色。
庭審結束了,判決和後續賠償不足以填補那段歲月的傷痛,我踏著沉重的步伐慢慢走下台階,這一切都太過漫長太過煎熬了。
我和其他親戚不熟,沒有人可以收留我,
後來被政府安置在一個管理式的收容住所。
見過許多專業人員與社工,但他們很多時候都不明白我的想法,只會照本宣科的用一套方式解讀我,從沒理解過我,甚至滿不在乎的傷害我。
我感到身心俱疲,
在獲救的兩年內,患有嚴重的PTSD和解離。
狀況不好經常住院,
這一住就是好幾個月,時間又被病情綁架走。
傾聽?真是可笑。
每當我強忍回憶說完那些慘無人道的痛苦時,
沒有一個人讓我感到放鬆自在,有的甚至不把我當一回事。
「好想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我本以為逃出來後,受到的傷害會減少,
但我錯了,身旁人的嘴臉同樣令我感到作嘔,
我努力想變成正常人,他們卻只希望我是個「沒發生任何事」的正常人。
我只是一個浪費社會資源的累贅,
我該死,不該活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是我真正的歸宿。
我的室友不在乎我是死是活,
說不定我不在她們反而更開心,
我就像是一個廢物惹人討厭又沒人愛。
「像這樣的自己根本沒有活下去的資格」
表現得很開心,被說不要做作,
表現得不開心,被說別裝可憐。
究竟要我怎樣做才滿意......?
是不是真的要我去死才滿意呢?
「說啊!!!站在我面前這樣告訴我啊!!!」
醫生:「妳如果不是真的想死,不要整天把這話掛在嘴邊」
是不是真的要我去死才滿意?呢......
妳怎麼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想死?憑什麼否定我?
「再說說看啊!!!妳們了解過我什麼了啊!!!?」
「像我這種骯髒低賤的人,本來就不會有人接受我的」
吊死在宿舍裡,說不定那些室友會憐憫一下我,
在你們惡語重傷我的時候,我真的痛到很想去死,
有的老師根本不配當老師,總是恣意妄為的評斷我,
從沒有母親溫暖的我,經常渴望能有人好好對待和愛我。
如果真的死了,這世界少了我說不定會更美好,
我的經歷圈粉不少,她們說我勇敢,我卻不這樣認為,
每當我想要去嘗試新事物時,身邊人總是想著要打擊我,
我的內心被狠狠踐踏,我果然還是去死不要給人添麻煩吧?
想要活下去真的好難,就連身邊接觸過我的人都不能夠理解。
(斜藏頭的香港髒話,O你O母死OOO男)
如果還嫌我受的傷不夠多,
那請把我殺死,一點痕跡都不留在這世界上,好嗎......?